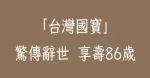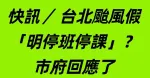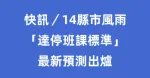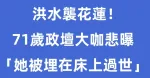3/3
下一頁
臨終前韋小寶攥著幾位夫人的手問:告訴我,哪個孩子是我親生的

3/3
韋小寶的腦子「嗡」的一聲,像是被看不見的重物狠狠砸了一下,眼前金星亂冒。這畫的哪裡是什麼狗屁「幼時嬉戲光景」,分明就是照著韋冬少年時的模樣畫的!連神態都分毫不差!
他下意識地猛地轉過頭,去看站在人群中的韋冬。
韋冬也正看著那幅畫,神情有些怔忡,似乎也看出了什麼。少年時的青澀已經從他臉上褪去,但他臉部的輪廓,眉眼間的神韻,和畫中人簡直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你瞧瞧!你瞧瞧!」建寧此刻正處於極度的興奮與感動之中,她拿著畫,像個終於得到心愛糖果的孩子,跑過來衝著韋小寶炫耀,完全沒注意到他煞白的臉色,「你這個死太監,睜大你的狗眼看看!皇兄心裡還是惦記著我的!皇兄才是對我最好的人!不像你,就知道守著你這一畝三分地,心裡哪還有我這個公主!」
「死太監」這個稱呼,是她以前在宮裡叫慣了的,帶著一股子施虐的快感。歸隱之後,韋小寶下了死命令,不許她再這麼叫,她已經很多年沒說過了。今天一激動,又脫口而出。
要是放在平時,韋小寶頂多也就是罵罵咧咧地回敬她幾句「瘋婆娘」,鬧一陣也就過去了。但今天,這三個字,加上眼前這幅意有所指的畫,就像一把燒紅的烙鐵,狠狠地、滋啦作響地燙在了他那顆本就已經千瘡百孔的心上。
一股混雜著滔天羞辱、無邊憤怒和刺骨恐懼的無名邪火,如同火山爆發一般,從他的腳底板直衝天靈蓋。他的理智,那根常年緊繃的弦,「啪」的一聲,徹底斷了。
他一把從建寧手裡搶過那幅被她視若珍寶的畫卷,一雙眼睛因為充血而變得通紅,死死地瞪著她,聲音因為極度的憤怒而嘶啞變形,像是從地獄裡傳出來的嘶吼:「他惦記你?他是惦記你,還是惦記他兒子?!」
這話一出口,整個屋子的人都驚呆了,時間仿佛靜止。欽差臉上的笑容僵住了,嘴巴半張,能塞進一個雞蛋。蘇荃臉色大變,厲聲喝道:「小寶!」雙兒更是嚇得捂住了嘴,渾身發抖。
建寧先是一愣,隨即像是被踩了尾巴的潑婦貓一樣,整個人都炸了起來。她那被歲月和安逸生活磨平的乖張暴戾,在這一刻全面復甦,甚至比年輕時更甚。
「韋小寶!」她發出足以刺破耳膜的尖叫,臉上血色盡褪,「你瘋了!你胡說八道什麼!你敢汙衊我,汙衊當今皇上!我跟你拼了!」
她張牙舞爪地就撲了上來,尖利的指甲直直地衝著韋小寶的臉撓去。韋小寶這次沒有像往常那樣躲閃或者讓著她,而是被憤怒沖昏了頭腦。他一把將建寧狠狠地推開,然後,在眾人驚恐的目光中,他雙手用力,將那幅康熙御筆的畫卷,「刺啦」一聲,撕成了兩半!
「我汙衊你?你自己乾的好事,你自己心裡清楚!」他指著不遠處的韋冬,歇斯底里地吼道,「你看看他!你再看看這畫!你當全天下都是瞎子嗎?啊?!」
「啊——!」建寧看到自己皇兄的御筆親繪被撕碎,像是被抽掉了最後一根主心骨,徹底瘋了。她哭喊著,廝打著,用所有她能想到的、最惡毒的語言咒罵著韋小寶。
房間裡頓時亂成了一鍋粥,下人們嚇得魂不附體,跪在地上瑟瑟發抖。欽差被夾在中間,臉上一陣青一陣白,恨不得自己當場瞎了聾了,或者直接昏死過去。
這場歸隱以來最激烈的爭吵,沒有贏家。只留下一地破碎的畫卷,兩個因為憤怒和絕望而面目全非的人,和一個被恐懼陰雲籠罩的家。
欽差眼看事情敗露到如此地步,早已嚇得三魂不見了七魄,找了個由頭,幾乎是連滾爬帶地逃出了韋府。他知道,自己無意中窺見了這個「皇親國戚」之家最可怕的秘密,這個秘密,足以要了他的命。
當天夜裡,韋小寶就倒下了。那場驚天動地的爭吵,徹底耗盡了他最後的一點元氣。
04
那場與建寧的激烈爭吵,像一陣狂風,不僅撕碎了康熙的畫,也徹底吹垮了韋小寶本就風雨飄搖的身體。
他病倒了,一病不起。
整日整日地躺在那張大床上,像是被釘在了上面。咳嗽變得越來越頻繁,也越來越重,有時候咳得撕心裂肺,會帶出血絲。請來的大夫換了一個又一個,從麗江本地的名醫,到蘇荃花重金從省城昆明請來的杏林國手,全都束手無策,開出的方子無非是些吊命的珍貴藥材。人參、靈芝、冬蟲夏草,像不要錢似的熬成湯藥,一碗碗地灌下去,卻也只能勉強維持著他那口氣不斷。
躺在床上,韋小寶的身體像一截被蟲蛀空了的朽木,但他的頭腦,卻在大多數時候異常地清醒。清醒得讓他痛苦。
關於韋虎和韋冬的疑雲,此刻在他心裡,已經不再是「懷疑」,而是板上釘釘的「事實」了。他覺得自己像個天底下最大的笑話,一個滑稽透頂的小丑。他為康熙皇帝賣了一輩子命,上刀山下火海,出生入死,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換來了這潑天的富貴和安逸。可到頭來呢?他最漂亮的夫人,給他戴了一頂綠油油的帽子,還可能讓他替頭號情敵養了二十年的兒子;他最尊貴的夫人,那個金枝玉葉的公主,更是膽大包天,直接讓他當了皇帝的「接盤俠」。
這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他韋小寶一輩子在女人堆里無往不利,自詡風流,沒想到老了老了,卻發現自己頭頂上綠草萋萋,都能跑馬了。
那股子羞辱感,像一把鈍刀,日日夜夜地在他心口上來回割,讓他不得安生。
他想起了自己的一生,從揚州麗春院裡一個任人打罵的小雜役,到今天這個富甲一方的韋老爺,靠的是什麼?是機靈,是會看人下菜碟,是懂得什麼時候該撒潑耍賴,什麼時候該裝孫子,什麼時候該挺身而出。說白了,就是懂得「裝糊塗」。可如今,他不想再糊塗下去了。他不能就這麼糊裡糊塗地死掉,變成一個糊塗鬼。
他咽不下這口氣。他不甘心。
他要證據,他要聽她們親口承認!
於是,他開始在病榻上,用他最後的力量,展開了一場無聲的調查。
他第一個找的,是他這一生最信任、最貼心的雙兒。在一個雙兒喂他喝藥的下午,他拉住雙兒的手,用微弱又沙啞的聲音對她說:「雙兒……我的好雙兒……你幫幫我……你去……你去聽聽,去看看……那些跟了阿珂和建寧多年的老媽子,她們一定知道些什麼。你賞她們金子,賞她們銀子,給她們的兒子家人安排好出路……只要她們肯說實話,要什麼都行。」
雙兒聽著他的話,眼淚撲簌簌地就掉下來了。她跪在床邊,把臉貼在他乾枯的手背上,哭得說不出話來。「相公,您別再想這些事了,好不好?再想下去,您的身子就真的垮了。孩子們……孩子們都是看著長大的,都是您的孩子,是咱們的孩子啊……」
她純粹的悲傷和不忍,像一盆冷水,澆在了韋小寶的心頭。他看著哭成淚人的雙兒,終究沒能狠下心來逼她。他知道,讓善良了一輩子的雙兒去做這種威逼利誘、探聽隱私的齷齪事,比殺了她還讓她難受。
雙兒這條路走不通,他又把主意打到了那些跟隨他多年的心腹管家身上。他把府里的大管家錢老本叫到床前。錢老本是他從揚州就帶出來的老人,對他忠心耿耿。
「老錢,」韋小寶喘著氣說,「我給你一千兩金子。你去辦件事。想辦法,撬開阿珂夫人和建寧公主院裡那幾個老人的嘴。我不要猜測,我要實打實的話。辦成了,我再給你兩千兩。」
錢老本「撲通」一聲跪在地上,老淚縱橫:「老爺!您這是要折殺老奴啊!老奴的命都是您給的,您讓老奴上刀山下油鍋,老奴眉頭都不皺一下。可是……可是這種事,老奴真的做不來啊!這後宅的事,是大夫人(蘇荃)在管,咱們……咱們插不上手啊!要是讓大夫人知道了,老奴死不足惜,只怕會攪得闔府不寧,反倒害了您的身子啊!」
韋小寶的心一點點地沉了下去。他慢慢地明白了。這個他親手建立起來的家,早就不完全是他的天下了。蘇荃,那個曾經的神龍教主夫人,用她超凡的智慧、手腕和威嚴,早已將這個後宅打理成了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鐵桶。在這個鐵桶里,女人們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維持這個家的「完整」和「體面」。
他,韋小寶,這個家的男主人,反而被她們聯手孤立了。他像一個坐在王座上的國王,卻發現自己的臣民們全都背著他達成了秘密的協議。
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無力感。
日子一天天過去,他的身體也一天天地衰敗下去。他開始整夜整夜地失眠,咳出來的血也從血絲變成了小口的血塊。他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對死亡的恐懼,像潮水一樣陣陣襲來,但比死亡更讓他恐懼的,是作為一個糊塗蛋死去的恥辱。
他必須知道真相。他不要再做一個明白鬼,他要在咽氣之前,就做一個明白人。
在一個深夜,韋小寶又經歷了一場劇烈的咳嗽,咳得他幾乎斷了氣。等他好不容易緩過一口氣來,他望著窗外那輪清冷孤高的月亮,渾濁的眼中,流露出一種令人心悸的、決絕的光芒。
他知道,用強的、用計的、用錢的,都沒用了。她們的聯盟堅不可摧。
他只剩下最後一樣武器了——他自己的「死」。
他要用自己彌留之際的最後一口氣,去撬開她們用幾十年光陰焊死的秘密。他要讓她們親口告訴他。這是一場賭局,他人生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場賭局,賭注是他一生的尊嚴。
「雙兒……」他用盡力氣,發出了微弱的呼喚。
一直在床邊椅子上打盹的雙兒猛地驚醒,連忙撲到床前,握住他的手:「相公,我在這裡,您怎麼了?」
「去……」韋小寶的嘴唇哆嗦著,每一個字都像是從牙縫裡擠出來的,「把她們……全都叫來。七個,一個……都不能少。告訴她們……就說我……我不行了……」
雙兒的心猛地一沉,她預感到了什麼。她看著韋小寶那張蒼白如紙,卻唯獨眼神亮得嚇人的臉,巨大的悲傷和恐懼攫住了她。但她知道,她無法違抗他,尤其是在這個時候。
她含著淚,重重地點了點頭:「是,相公。」
很快,韋小寶的臥房裡,燈火通明。七位夫人陸續到來,她們的腳步都很輕,仿佛怕驚擾了什麼。她們看著床上那個氣若遊絲,仿佛隨時都會咽氣的男人,每個人的臉上都帶著不同的複雜情緒——有悲傷,有恐懼,有憐憫,但更多的,是一種心照不宣的、深深的戒備。
一場最後的審判,即將開始。而審判者,卻是那個即將走向生命盡頭的人。
05
韋小寶的臥房裡,靜得能聽見燈芯在燈油里燃燒時發出的輕微「噼啪」聲,還有窗外偶爾傳來的幾聲蟲鳴。濃重的湯藥味混合著死亡的腐朽氣息,瀰漫在空氣中,壓得人喘不過氣。
七個女人,七個曾經攪動了他整個人生,與他命運緊緊糾纏在一起的女人,此刻都圍在了他的床邊。她們有的曾是他的敵人,有的曾是他的摯愛,有的曾是他強取豪奪的對象。如今,她們都是他的夫人,是他這個龐大家族的共同支柱。
韋小寶的胸口劇烈地起伏著,每一次呼吸都帶著沉重而嘶啞的風箱聲。他感覺自己的生命就像一個已經見底的沙漏,正在飛快地流逝著最後一縷沙。他必須抓緊時間。
他顫抖著,費力地伸出那隻枯瘦如柴、布滿青筋的手。
一直守在床邊的雙兒和站在最前面的蘇荃立刻上前,一左一右,握住了他冰冷的手。那隻曾經在皇宮裡偷雞摸狗,在賭場裡搖擲乾坤,在戰場上指點江山的手,如今瘦得只剩下皮包骨頭,輕飄飄的,毫無力氣。
他的目光,像一盞即將燃盡的油燈,吃力地、緩緩地掃過眼前的每一個女人。
他看到了蘇荃,她依舊端莊,但緊鎖的眉頭和緊抿的嘴唇泄露了她內心的緊張與決斷。他看到了雙兒,她眼中全是心碎與不忍,淚水在眼眶裡打轉,隨時都會落下。他看到了建寧,她站在稍遠的地方,眼神里充滿了怨恨和一絲不易察อก的躲閃,手指緊張地絞著衣角。他看到了阿珂,她站在人群的最後面,垂著頭,臉色蒼白得像一張紙,整個人仿佛是一尊沒有靈魂的玉像,散發著生人勿近的寒氣。他還看到了方怡、沐劍屏和曾柔,她們臉上交織著惶恐、茫然與不知所措。
她們的表情各不相同,卻又像一張無形的、堅韌的網,共同守護著一個他拼了命也想要觸碰到的中心。
韋小寶深吸一口氣,這一口氣仿佛抽乾了他全身最後殘存的力氣。
他的聲音很輕,很沙啞,卻像一把鋒利的錐子,一字一字地鑿進了在場每個人的心裡:
「我……我裝糊塗了大半生……你們……你們告訴我……」
他停頓了一下,積攢著力氣。他那雙渾濁的眼睛裡,突然迸發出一股令人心悸的光芒,那光芒里有憤怒,有不甘,有羞辱,但更多的,是一種近乎乞求的絕望。
「……哪幾個孩子……是我親生的?」
石破天驚。
整個房間的空氣,在這一句話問出口的瞬間,徹底凝固了。時間仿佛被凍結,萬籟俱寂,只剩下韋小寶那因為耗盡力氣而愈發粗重的喘息聲。
這句他已經在心裡反覆咀嚼、反覆吞咽了無數遍的話,終於還是像一顆燒紅的烙鐵,被他從滾燙的胸膛里掏了出來,狠狠地印在了這死寂的空氣中。它像一顆投入死水潭的巨石,激起了滔天的巨浪,將所有虛假的平靜和多年的偽裝撕得粉碎。
第一個做出反應的是雙兒。她的心理防線在這一刻徹底崩潰,眼淚瞬間決堤,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滾落下來,滴在韋小寶乾枯的手背上,滾燙得嚇人。
「相公!」她哭著喊道,聲音里充滿了無法言喻的痛苦,「您……您怎麼能這麼問!您要我們的心疼死嗎?我們的孩子……當然都是您的啊!您別胡思亂想了,相公!別想了!」
她的悲傷是如此純粹,如此真實,不帶任何雜質,像一把小刀,剜著在場每個人的心。
緊接著,建寧像是被踩了尾巴的潑婦貓,整個人都炸了起來,尖聲叫嚷道:「韋小寶!你都要死了還在這裡疑神疑鬼!本公主的孩子,龍子鳳孫,還能有假不成?你這是在咒我,還是在咒你自己?你安的什麼心!」
她的聲音又高又尖,帶著一種色厲內荏的虛張聲勢。她似乎覺得,只要自己的聲音足夠大,就能掩蓋住內心的恐懼和心虛,就能證明自己的清白。
而阿珂,她的反應最為劇烈,也最為安靜。在韋小寶問出那句話的瞬間,她的臉色「唰」地一下,變得慘白如紙,沒有一絲血色。
她的身體晃了一下,幾乎要站立不穩,幸好被身邊的曾柔扶了一把。她的嘴唇無聲地翕動了幾下,卻一個字也發不出來。她只是死死地攥住了自己的衣角,指節因為過度用力而發白。她垂下眼帘,長長的睫毛在燭光下投下一片濃重的陰影,整個人像一尊即將在下一秒無聲碎裂的玉像。她不敢看韋小寶,也不敢看任何人。
方怡和曾柔下意識地對視了一眼,都從對方眼中看到了同樣的驚慌失措。她們像是被突然捲入風暴中心的兩葉小舟,完全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沐劍屏更是嚇得小臉發白,她不懂這裡面複雜的糾葛,只是本能地感到害怕,怯生生地抓住曾柔的衣袖,小聲說:「小寶哥哥……你別嚇我們……大家……大家會害怕的……」
一片混亂中,只有蘇荃,還保持著最後的鎮定。
她眉頭緊鎖,臉色凝重。她先是安撫性地用力拍了拍韋小寶的手背,示意他冷靜,然後,她那雙經歷過大風大浪、依舊銳利如鷹的眼睛,像刀子一樣掃過房間裡亂作一團的姐妹們。
「都住口!」她沉聲喝道。
這一聲,分量十足,充滿了不容置喙的威嚴。建寧的尖叫戛然而止,雙兒的哭聲也小了下去。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集中在了她的身上,仿佛她才是這裡的主心骨。
蘇荃轉向韋小寶,神色複雜地看著他,語氣裡帶著一絲疲憊和沉重:「小寶,你這又是何苦。你這一輩子,有什麼天大的事,不是嘻嘻哈哈就混過去了?怎麼臨到頭了,非要鑽這個牛角尖。孩子們都是你的,是我們大家的孩子,這個家還在,這還不夠嗎?」
她的話,條理清晰,意有所指,像是在努力地把那個被韋小寶硬生生撕開的口子重新糊上。
但韋小寶不為所動。他知道,這是他最後的機會,一旦錯過,他將死不瞑目。他用盡全力,從喉嚨里擠出幾個字,那雙已經開始渙散的眼睛,卻越過蘇荃,死死地鎖在那個從頭到尾一言不發、如同雕像般的阿珂身上。
「阿珂……你先說。」
他的聲音微弱,卻帶著一股不得到答案絕不罷休的偏執和狠勁。
「虎兒……他……他到底是不是我的?」
整個房間,再一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落針可聞。
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探照燈一樣,齊刷刷地聚焦在了阿珂那張慘白如雪的臉上。她整個人都在無法控制地發抖,嘴唇哆嗦得厲害,似乎在與內心某種巨大的、折磨了她二十多年的力量進行著最後的抗爭。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空氣仿佛凝結成了冰,每一秒都像一年一樣漫長。
終於,阿珂像是下定了某種決心,又像是徹底放棄了抵抗。她緩緩地、極為艱難地抬起頭,迎向了韋小寶的目光。她的眼中沒有了之前的空洞和麻木,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令人心碎的、決絕的悲哀。她張開那早已沒有血色的嘴唇,似乎就要開口……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蘇荃突然上前一步,像一堵牆,穩穩地擋在了阿珂和韋小寶之間。
她的動作並不快,卻帶著一種斬釘截鐵、不容商量的決斷力。她對著床上那個即將油盡燈枯的男人,也像是對著在場的所有姐妹,一字一句地,清晰無比地說道:
「小寶,這件事,不是她們任何一個人的事。」
她頓了頓,環視了一圈眾人,加重了語氣:
「是我們七個姐妹,早就有了約定的事。」
她最後看向韋小寶,目光深沉如海:
「你何苦,非要再問?」
「約定?」
韋小寶的腦子「嗡」的一聲,幾乎停止了思考。什麼約定?她們之間……有什麼約定?他看著擋在自己面前,身形依舊挺拔、氣場強大的蘇荃,又越過她的肩膀,看向她身後那一張張神色各異、或驚恐、或悲傷、或麻木的臉。
他突然間明白了什麼。
這件事,遠比他想像的要複雜,要龐大。
這根本不是一個或者兩個女人的偶然背叛。
而是一個由他所有女人共同參與、共同保守了二十多年的,巨大的,深不見底的秘密。
這個秘密,到底是什麼?
蘇荃的話,像一扇剛剛被推開一絲縫隙的沉重鐵門,門縫裡透出的不是他渴求的光明,而是無盡的、令人窒息的黑暗。那個黑暗的深處,藏著他這個家的根基,也可能藏著足以將他徹底摧毀的真相。
06
「什麼……約定?」
韋小寶用盡全身的力氣,從喉嚨里擠出這幾個字。他的眼睛死死地盯著蘇荃,那雙渾濁的眼睛裡,寫滿了震驚、迷惑和一絲即將被真相吞噬的恐懼。他感覺自己像一個在黑暗中摸索了半輩子的人,馬上就要摸到那扇終極之門的門把手了。
蘇荃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似乎也在為接下來的話積攢勇氣。她轉過身,先是看了看臉色煞白的阿珂,又看了看一臉倔強卻同樣在發抖的建寧,最後,她的目光落在了哭得幾乎要暈厥過去的雙兒身上,眼神中閃過一絲憐憫和不忍。
她重新轉向韋小寶,聲音低沉而清晰,開始講述一個被塵封了將近二十年的往事。
「小寶,你還記不記得,咱們剛歸隱到麗江的第五個年頭。」蘇荃緩緩開口,她的聲音像是有魔力,讓整個房間的嘈雜和慌亂都平息了下來,「那一年,雲南大亂。一些不甘心的天地會舊部,勾結上了吳三桂的殘黨和地方上的土匪,在滇西一帶鬧得很大,燒殺搶掠,連官府都焦頭爛額。」
韋小寶的眼神有些迷茫,他在費力地回憶。那段日子,他確實不在家。他以為自己的身份早已洗白,可以高枕無憂,沒想到江湖上的恩怨還是找上了門。他不想讓朝廷插手,暴露自己的行蹤,只好親自出馬,帶著幾個從京城帶來的高手,去平息那場動亂。
蘇荃看著他的表情,知道他想起來了。她繼續說道:「你這一去,就是將近半年。剛開始還有消息斷斷續續傳來,後來,有兩個月的時間,你音訊全無。再後來……從外面傳來了消息,說你……說你中了亂黨的埋伏,已經……已經死在了哀牢山里。」
說到「死」字,雙兒的哭聲又忍不住大了起來,阿珂的身體也再次劇烈地顫抖了一下。那是韋家所有人都不願回憶的一段黑暗時光。
「你死了的消息傳回來,整個韋家大院,天都塌了。」蘇荃的眼神變得悠遠,仿佛又回到了那個風雨飄搖的時刻,「外面,那些亂黨和地方上的豪強,都像聞到血腥味的狼,盯著我們這家裡的萬貫家財,蠢蠢欲動。府里,下人們人心惶惶,一些手腳不幹凈的開始偷盜,一些有野心的管事開始拉幫結派,都想在你倒下後分一杯羹。我們這群女人,帶著一群半大的孩子,就像是待宰的羔羊。」
韋小寶靜靜地聽著,他從來不知道,在他看不到的地方,他的家,他的女人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危機。他一直以為她們在他的羽翼下,過得無憂無慮。
「那段時間,建寧整天哭著鬧著要回京城找皇兄,阿珂心灰意冷,把自己關在房裡不見任何人。方怡和曾柔她們也是六神無主,只有雙兒,一邊哭一邊還撐著,照顧孩子,安撫下人。」
「我看著這個即將分崩離析的家,我知道,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你不在了,我們要是再不擰成一股繩,不出三天,我們這群女人和孩子,就會被外面的豺狼虎豹吃得連骨頭渣子都不剩。」
蘇荃的眼中閃過一絲當年身為教主夫人時的狠厲和果決。
「於是,我把她們六個,全都叫到了我的房間裡。我關上門,跟她們進行了一次長談。我告訴她們,韋小寶是生是死,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們這群女人和這些孩子,要活下去。要想活下去,就不能再分彼此,不能再有私心。」
她的聲音變得莊嚴而肅穆,像是在宣讀一份神聖的誓言。
「就在那個晚上,我們七個姐妹,點上了香,對著關二爺的神像,立下了一個盟約。」
蘇荃看著韋小寶的眼睛,一字一句,清晰無比地說道:
「我們七個人對天發誓,從今往後,我們七姐妹榮辱與共,生死相依。這個家裡,就是我們共同的家。這個家裡所有的孩子,無論他的來處如何,無論他到底是誰的骨血,都只有一個爹,那就是韋小寶!他們都姓韋,都是韋家的子孫!我們七個人,就是所有孩子的娘!」
「盟約的最後一條是,誰要是敢向外人,包括向你韋小寶,泄露關於孩子身世的半個字,誰要是敢因為這些事挑起內鬥,破壞這個家,就叫她天打雷劈,五馬分屍,永世不得超生!」
這番話說完,整個房間陷入了更深沉的寂靜。建寧低下了頭,方怡和沐劍屏她們更是泣不成聲。這個當年為了自保而立下的惡毒誓言,像一道無形的枷鎖,捆綁了她們二十年。
韋小寶怔怔地聽著,心裡五味雜陳,像打翻了一整個調料鋪。他原以為,自己面對的是單純的姦情和背叛,他準備好去承受那份羞辱和憤怒。可他萬萬沒有想到,真相的背後,竟然是這樣一段為了生存而結下的、充滿了悲壯和無奈的女人之間的同盟。
他的憤怒,在這一刻,被一種更深沉、更複雜的悲哀所取代。他發現,在他看不到的地方,在他自以為是的掌控之外,他的女人們,也經歷了她們自己的「江湖」,她們的「刀光劍影」,甚至比他在外面經歷的更加兇險。
蘇荃沒有給他太多消化的時間,她知道,既然開了這個頭,就必須把話說完。
「阿珂,」她轉向阿珂,聲音放緩了一些,「當年,在你以為小寶已經死了,萬念俱灰的時候,鄭克塽輾轉找到了雲南來,想帶你走。你和他……有過一次會面。那時的你,孤苦無依,心神大亂,一時糊塗……」
她沒有把話說得太透,但意思已經再明白不過。
「還有建寧,」她又看向建寧,「你那次回京省親,正是小寶在外面為了平定神龍教餘孽的叛亂,長達一年沒有回家的時期。你們夫妻失和,你一個人在宮裡孤單寂寞,皇上……他對你這個唯一的妹妹多有撫慰,關心備至。深宮大內,皇家秘辛,孤男寡女,誰又能說得清那裡面的對與錯。」
蘇荃最後看著韋小寶,眼中滿是疲憊:「小寶,這些事,有的是發生在你『死』後,有的是發生在你對她們冷落疏遠之時。我們立下那個盟約,就是決定,把所有這些可能會毀了這個家的『過去』,全部埋葬。我們選擇集體沉默,共同撫養所有的孩子,把他們都當成是你的孩子來養大,只為了保護這個來之不易的、能讓我們所有人安身立命的家。」
「我們不是為了騙你一個人,」蘇荃的聲音裡帶著一絲顫抖,「我們是為了騙過所有人,騙過這個吃人的世道,甚至……騙過我們自己。只要我們自己信了,這個家,就還是完整的。」
07
蘇荃的話,像一陣沉重而悲涼的晚鐘,在韋小寶的耳邊久久迴響。
盟約。
原來如此。
他明白了為什麼這個家像個鐵桶,為什麼所有人都守口如瓶。原來,這不是一兩個人的背叛,而是一場由他所有女人共同參與的、為了生存而進行的「合謀」。
他的心裡,那股子沖天的怒火,被這悲涼的真相澆熄了大半,只剩下一點點不甘心的火星,和一片茫然的灰燼。他覺得自己像個在台下看戲的看客,一直以為台上演的是一出風流喜劇,到最後才發現,那其實是一出充滿了血淚和掙扎的悲劇,而他自己,既是戲裡的主角,又是唯一被蒙在鼓裡的傻子。
可是,他還是不甘心。
盟約是盟約,事實是事實。他已經沒有幾天好活了,他要聽的不是這個冠冕堂皇的「盟約」,他要的是那個最原始、最赤裸的「事實」。他要死得明明白白。
他掙扎著,從喉嚨里發出嗬嗬的聲音,眼睛死死地盯著蘇荃,又越過她,看向她身後的阿珂和建寧。他的眼神在說:我要聽她們親口說。
蘇荃讀懂了他的眼神。她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那口氣里,有疲憊,有解脫,也有一種宿命般的無奈。她知道,這個秘密守了二十年,終究還是到了要揭開的時候。也好,說開了,對所有人來說,或許都是一種解脫。
她默默地向後退了一步,讓開了位置,將舞台的中央,留給了那兩個秘密的核心。
所有的目光,再次聚焦在阿珂身上。
阿珂的身體抖得更厲害了。蘇荃的話,像是一把鑰匙,打開了她塵封了二十年的心牢。牢里關著的所有愧疚、悔恨、痛苦和恐懼,在這一刻奔涌而出,瞬間將她淹沒。
她再也支撐不住,雙腿一軟,「撲通」一聲,跪倒在韋小寶的床前,距離他不過幾尺之遙。
「我……我說……」她的聲音嘶啞得像被砂紙磨過,每一個字都帶著血淚,「我對不起你……」
她抬起頭,那張曾經絕美無雙的臉上,此刻布滿了淚痕,眼中是深不見底的絕望。「荃姐姐說的沒錯……那年,傳來你的死訊,我以為你真的死了。我覺得天都塌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就在那個時候,他……鄭克塽找到了我。」
「他說他後悔了,他說他這些年一直派人打探我的消息,他說他被流放關外,九死一生,心裡想的念的全是我。他說要帶我走,去一個沒人認識我們的地方,重新開始……我當時……我當時真的撐不住了……我覺得,既然你死了,我活著也沒什麼意思,不如就跟他走了……」
她泣不成聲,斷斷續續地說道:「就……就一次……就那麼一次……我便懷上了虎兒。可事後,我清醒過來,我就後悔了。我恨他,更恨我自己。我沒臉去見你,更沒臉活下去。是荃姐姐……是荃姐姐她們拉住了我,她們跟我說了那個盟約。她們說,為了孩子,為了虎兒能有一個堂堂正正的身份,而不是一個私生子,為了這個家不散,我必須把這個秘密爛在肚子裡。」
她一邊哭,一邊重重地對著韋小寶磕頭,額頭撞在冰冷的地板上,發出沉悶的響聲。
「我對不起你……韋小寶,我對不起你!但我……我更對不起虎兒!他這一輩子,都活在一個謊言里,他連自己的親生父親是誰,都不知道……」
阿珂的坦白,像一把尖刀,狠狠地扎進了韋小寶的心裡。雖然早已猜到,但親耳聽見,那種感覺還是不一樣。那是一種被證實了的、赤裸裸的羞辱。但他看著跪在地上,哭得幾乎要死過去的阿珂,心裡卻生不出一絲一毫的恨意,只剩下無盡的悲涼。
他沒有說話,只是轉動眼珠,將目光投向了另一個當事人——建寧公主。
建寧沒有跪。
她只是靜靜地站在那裡,臉上的囂張和乖張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深可見骨的疲憊和麻木。她迎著韋小寶的目光,沒有躲閃。
「看我做什麼?」她開口了,聲音很平靜,甚至帶著一絲自嘲的笑意,「你不是都猜到了嗎?」
她抬手,輕輕擦了擦眼角,說道:「沒錯,韋冬,他是皇兄的兒子。」
她的話,比阿珂的更直接,更不加掩飾。
「那次回宮,我感覺自己又活過來了。」她的眼神有些飄忽,像是在回憶遙遠的過去,「在雲南,我是你的老婆,是韋夫人,我要守你那一大家子的規矩,要看蘇荃的臉色。可是在紫禁城,我還是那個高高在上的建寧公主,皇兄……他對我很好,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好。他會陪我說話,陪我散步,聽我抱怨你的種種不是。他說我受委屈了。」
「那是一場心照不宣的錯誤。」她的臉上露出一個複雜的、說不清是甜蜜還是苦澀的笑容,「我不是為了背叛你,韋小寶。我只是……我只是想做回我自己。哪怕只有一次。我想找回那種被人捧在手心裡的感覺,找回做公主的感覺,而不是你韋小寶七個老婆里的一個。」
她說完,就沉默了,仿佛已經說完了她這輩子最想說的話。
阿珂和建寧的坦白,像推倒了第一塊多米諾骨牌。
方怡哭著上前一步,也跪了下來:「老爺,我……我雖然沒有做出越軌之事,但荃姐姐立下盟約的時候,我是同意的,我發了毒誓。我……我對不起您……」
曾柔和沐劍屏也跟著跪下,哭成一團。她們雖然天真單純,但也知道,守護這個秘密,本身就是對韋小寶的一種欺騙。
雙兒更是哭得肝腸寸斷。她一邊替韋小寶感到委屈和心痛,一邊又替這些命運多舛的姐妹感到悲哀。她撲在床邊,握著韋小寶的手,哽咽道:「相公……她們……她們也是沒辦法……您就……您就原諒她們吧……」
整個房間,充斥著女人們壓抑的哭聲和懺悔聲。
韋小寶得到了他想要的真相,一個又一個。這些真相像一把把雙刃劍,刺向了他,也狠狠地刺向了坦白的每一個人。他像是終於解開了一個困擾他一生的謎題,但看到謎底的那一刻,隨之而來的,卻是比謎題本身更加巨大的空虛、荒謬和悲涼。
他一生汲汲營營,費盡心機追求的「齊人之福」,他引以為傲的「妻妾成群,兒女滿堂」,原來,只是一個由謊言、秘密和女人的眼淚精心構建起來的、看似華美實則脆弱的空中樓閣。
而他,就是那個住在閣樓里,還自以為是天下最幸福的傻子。
08
知道了所有的真相之後,韋小寶陷入了長久的、死一般的沉默。
他不再說話,也不再看任何人。他就那麼睜著眼睛,空洞地望著頭頂上方的明黃色帳幔,那上面用金線繡著繁複的龍鳳呈祥圖案,此刻在他看來,充滿了無盡的諷刺。
房間裡的哭聲漸漸小了下去,只剩下壓抑的抽泣。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緊張地看著他。她們都在等待著,等待著他最後的審判。她們以為,他會爆發出最後的、雷霆萬鈞的憤怒,會用最惡毒的語言咒罵她們,然後在一場驚天動地的怨恨中死去。
畢竟,他是韋小寶。一個受了奇恥大辱的男人。
可是,他沒有。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久到仿佛連空氣都開始感到疲憊。
突然,韋小寶的嘴角,向上牽動了一下。他笑了。
那是一個極其古怪的笑容,比哭還難看,卻又帶著一絲說不清道不明的意味。他笑著,喉嚨里發出「嗬嗬」的聲音,隨即引發了一陣劇烈的咳嗽。
「咳咳……咳咳咳……」他咳得滿臉漲紅,幾乎要喘不上氣來。
「相公!」雙兒驚呼著,連忙替他撫背順氣。
好半天,韋小寶才緩了過來。他無力地擺了擺手,示意跪了一地的女人們都起來。他的聲音,比之前任何時候都要微弱,卻也平靜得不可思議。
「都……都起來吧……跪著做什麼……地上涼……」
女人們將信將疑地站起身,面面相覷,都不知道他這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藥。
韋小寶的目光,緩緩地從她們身上移開,投向了被這邊的動靜驚動,正站在門口,一臉驚惶和不知所措的韋虎和韋冬。
「虎兒……冬兒……過來……」他朝他們招了招手。
韋虎和韋冬對視一眼,猶豫著走了進來。他們的臉色都很蒼白,顯然,剛才房裡的對話,他們已經聽到了大半。這對他們來說,不啻於天塌地陷。
兩人走到床前,默默地跪下,低著頭,不敢看韋小寶。
韋小寶伸出那隻已經沒有多少溫度的手,先是摸了摸韋虎的頭。韋虎渾身一僵。
「好小子……」韋小寶的聲音很輕,「長得……長得真俊……像你……像你娘……」
他的話里,沒有一絲一毫的怨恨和責備,反而像一個普通的、行將就木的父親,對自己孩子最質樸的誇讚。韋虎的肩膀劇烈地顫抖起來,他把頭埋得更低了,滾燙的淚水砸在了地板上。
然後,韋小寶又把手轉向韋冬,吃力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你這孩子,有出息……像……像個做大事的人……」他喘了口氣,繼續說道,「以後……以後我不在了……你和你大哥……要撐起這個家……要照顧好你們的娘……和……和弟弟妹妹們……」
他對他們,沒有一句質問,沒有一句責備,反而像一個最尋常的父親一樣,平靜地交代著後事。
在場的所有人,都怔住了。她們不懂,韋小寶為什麼不生氣,為什麼不憤怒。
只有蘇荃,看著韋小寶那雙已經開始渙散的眼睛,似乎隱隱明白了一些什麼。
韋小寶又把目光轉回到他的女人們身上。他再次費力地伸出雙手,蘇荃和雙兒再次握住。他攥著她們的手,目光一個一個地看過去,像是要把她們的模樣,刻進自己的靈魂里。
最後,他那幾乎已經沒有焦距的眼睛,看著帳幔,斷斷續續地,像是對自己說,又像是對所有人說:
「親生的……不親生的……又……又能怎麼樣呢……」
「養了……養了這麼多年……有哭……有笑……有吵……有鬧……」
「在我韋家的屋檐下長大……吃我韋家的飯……叫我一聲爹……那……就都是我的種……」
他似乎是想笑一下,卻已經沒有力氣了。
「挺好……這樣……挺好……」
他的目光,最後轉向了一直握著他手的蘇荃,輕輕地點了點頭。那一個點頭,包含了太多複雜的情緒。有埋怨,有諒解,但更多的,似乎似乎是一種遲來的感謝。感謝她,用她的鐵腕和智慧,維繫住了這個看似荒唐卻又無比真實的「家」。
然後,他用盡最後一絲力氣,轉過頭,看向了他生命中唯一的、也是永遠的港灣——雙兒。
雙兒正滿臉淚水地看著他,眼中是無盡的眷戀和心痛。
韋小寶的嘴唇動了動,他想對她說句什麼。或許是想說一句「對不起」,因為他知道,在這所有的妻妾里,唯有雙兒,對他奉獻了全部的、毫無保留的愛與忠誠,而他,卻帶給了她這樣一個充滿了欺騙和秘密的家庭。又或許是想說一句「謝謝你」,謝謝她一輩子的陪伴和不離不棄。
可是,他終究什麼也沒能說出口。他的喉嚨里發出了一聲輕微的、像是嘆息一樣的聲響,然後,他的身體徹底放鬆了下來,那雙一直努力睜著的眼睛,緩緩地、永遠地閉上了。
那隻緊緊攥著雙兒和蘇荃的手,也隨之失去了最後的力氣,無力地滑落。
「相公——!」
雙兒發出一聲悽厲的哭喊,撲倒在韋小寶的身上,痛不欲生。
整個房間,瞬間被巨大的、無法抑制的哭聲所淹沒。阿珂跪在地上,哭得渾身抽搐;建寧捂著臉,發出了壓抑而痛苦的嗚咽;方怡、曾柔、沐劍屏相擁而泣。韋虎和韋冬跪在床前,額頭抵地,肩膀劇烈地聳動著。
這個攪動了大清半個世紀風雲,從揚州的地痞流氓,一路奇遇,做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鹿鼎公韋小寶,就這麼走了。
他裝糊塗過了一生,臨死前,偏執地求一個明白。
可當他真的得到了這個「明白」之後,才發現,原來「糊塗」才是他這一生最大的福氣。
他一直以為,他用自己的權勢、金錢和手段,征服了這些女人,擁有了她們。可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才恍然大悟,不是他擁有了她們,而是她們所有人,用各自的犧牲、隱忍和謊言,共同「擁有」了他所構建的這個可以遮風避雨的家。
這個家,雖然根基建立在謊言之上,但幾十年的朝夕相處,幾十年的吵吵鬧鬧,幾十年的互相扶持,那份早已滲透進骨血里的親情和羈絆,早已比那虛無縹緲的血緣,更加堅韌,更加真實。
親生的,不親生的,又如何呢?
他韋小寶,終究還是做了一回「明白鬼」。而這個明白,沒有帶給他怨恨,只帶給了他最後的、荒誕的平靜。
或許,對他來說,這便是最好的結局。
韋小寶的喪事,辦得極其隆重,甚至有些鋪張。整個麗江城,但凡有頭有臉的人物都前來弔唁。出殯那天,送葬的隊伍從韋府門口一直排出去了好幾里地。
喪事由蘇荃一手操持,辦得井井有條,滴水不漏,讓所有人都見識到了這位韋家大夫人的手腕和威儀。
靈堂設在正廳,正中懸掛著韋小寶的畫像。畫像上的他,還是中年時的模樣,穿著一品大員的朝服,臉上帶著那標誌性的、似笑非笑的表情,眼神里透著一股子機靈和狡黠,仿佛隨時都會從畫里跳出來,說一句:「奶奶的,哭什麼哭,老子還沒死透呢!」
韋豹、韋虎、韋冬等幾個兒子,身穿重孝,跪在靈前,為前來弔唁的賓客一一還禮。他們的臉上都帶著悲傷,但神情卻很平靜。
尤其是韋虎和韋冬,在經歷了那一夜的天崩地裂之後,他們仿佛一夜之間長大了。他們看彼此的眼神,沒有了往日的競爭和隔閡,反而多了一種同病相憐、相依為命的默契。
七位夫人一身素服,站在靈堂的側面。她們的眼睛都哭得紅腫,但沒有一個人失態。她們只是靜靜地站著,像七座沉默的雕像,共同送別那個讓她們又愛又恨了一輩子的男人。
喪事過後,生活似乎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但所有人都知道,有些東西,已經永遠地改變了。
一天下午,陽光正好。
蘇荃處理完府中的帳目,感到有些疲憊,便一個人來到後花園的涼亭里歇息。雙兒端著一碗剛燉好的燕窩,悄悄走了過來。
「荃姐姐,累了吧,喝點東西潤潤喉。」
蘇荃接過燕窩,卻沒有喝,只是用勺子輕輕攪動著。她看著滿園在陽光下盛開的花朵,輕聲問道:「雙兒,你……你怪我嗎?」
雙兒愣了一下,隨即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搖了搖頭,在蘇荃身邊坐下,柔聲說:「不怪。我知道,姐姐這麼做,都是為了這個家,為了我們大家。」她頓了頓,眼中泛起淚光,「我只是……只是心疼相公。他這一輩子,活得太累了。」
蘇含聞言,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眼中也流露出一絲悲戚:「是啊,他活得累,我們又何嘗不累呢?守著一個天大的秘密,守了幾十年,日日夜夜,如履薄冰。現在,他走了,我們……也算是解脫了。」
兩人沉默了片刻。
「那天晚上,」雙兒輕聲問,「相公他最後……是不是明白了什麼?」
蘇荃抬起頭,看向不遠處。韋虎和韋冬正並肩走在小徑上,不知在說些什麼。韋虎還是那般俊朗,但眉宇間多了幾分沉穩;韋冬還是那般氣度不凡,但眼神里卻少了幾分疏離,多了一絲屬於這個家的溫情。
蘇荃的臉上,露出了一個極其複雜的、混雜著欣慰與悲涼的笑容。
她緩緩地,卻又無比篤定地說道:「他明白了。」
「他最後,是明白了。糊塗了一輩子,臨死前,他終於做了一回真正的明白人。他明白,這個家,就是他的家。這些孩子,就是他的孩子。血緣……有時候,並沒有那麼重要。」
陽光穿過亭子的飛檐,在青石地面上投下斑駁的光影。遠處的草場上,又傳來了孩子們的嬉笑聲和打鬧聲。新一代的韋家子孫,正在無憂無慮地成長。
韋家大院,依舊是那個富麗堂皇、人丁興旺的韋家大院。
生活,還要繼續。
只是那個給這個家帶來了一切財富與榮耀,也帶來了一切紛爭與秘密的男人,已經永遠地睡著了。
在他走後,這個由謊言維繫的家,反而因為真相的揭開,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堅固。因為所有人都知道,他們如今所擁有的一切,都是用那個男人的妥協,和她們所有人的青春、眼淚與秘密,共同換來的。
他們,再也分不開了。
他下意識地猛地轉過頭,去看站在人群中的韋冬。
韋冬也正看著那幅畫,神情有些怔忡,似乎也看出了什麼。少年時的青澀已經從他臉上褪去,但他臉部的輪廓,眉眼間的神韻,和畫中人簡直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你瞧瞧!你瞧瞧!」建寧此刻正處於極度的興奮與感動之中,她拿著畫,像個終於得到心愛糖果的孩子,跑過來衝著韋小寶炫耀,完全沒注意到他煞白的臉色,「你這個死太監,睜大你的狗眼看看!皇兄心裡還是惦記著我的!皇兄才是對我最好的人!不像你,就知道守著你這一畝三分地,心裡哪還有我這個公主!」
「死太監」這個稱呼,是她以前在宮裡叫慣了的,帶著一股子施虐的快感。歸隱之後,韋小寶下了死命令,不許她再這麼叫,她已經很多年沒說過了。今天一激動,又脫口而出。
要是放在平時,韋小寶頂多也就是罵罵咧咧地回敬她幾句「瘋婆娘」,鬧一陣也就過去了。但今天,這三個字,加上眼前這幅意有所指的畫,就像一把燒紅的烙鐵,狠狠地、滋啦作響地燙在了他那顆本就已經千瘡百孔的心上。
一股混雜著滔天羞辱、無邊憤怒和刺骨恐懼的無名邪火,如同火山爆發一般,從他的腳底板直衝天靈蓋。他的理智,那根常年緊繃的弦,「啪」的一聲,徹底斷了。
他一把從建寧手裡搶過那幅被她視若珍寶的畫卷,一雙眼睛因為充血而變得通紅,死死地瞪著她,聲音因為極度的憤怒而嘶啞變形,像是從地獄裡傳出來的嘶吼:「他惦記你?他是惦記你,還是惦記他兒子?!」
這話一出口,整個屋子的人都驚呆了,時間仿佛靜止。欽差臉上的笑容僵住了,嘴巴半張,能塞進一個雞蛋。蘇荃臉色大變,厲聲喝道:「小寶!」雙兒更是嚇得捂住了嘴,渾身發抖。
建寧先是一愣,隨即像是被踩了尾巴的潑婦貓一樣,整個人都炸了起來。她那被歲月和安逸生活磨平的乖張暴戾,在這一刻全面復甦,甚至比年輕時更甚。
「韋小寶!」她發出足以刺破耳膜的尖叫,臉上血色盡褪,「你瘋了!你胡說八道什麼!你敢汙衊我,汙衊當今皇上!我跟你拼了!」
她張牙舞爪地就撲了上來,尖利的指甲直直地衝著韋小寶的臉撓去。韋小寶這次沒有像往常那樣躲閃或者讓著她,而是被憤怒沖昏了頭腦。他一把將建寧狠狠地推開,然後,在眾人驚恐的目光中,他雙手用力,將那幅康熙御筆的畫卷,「刺啦」一聲,撕成了兩半!
「我汙衊你?你自己乾的好事,你自己心裡清楚!」他指著不遠處的韋冬,歇斯底里地吼道,「你看看他!你再看看這畫!你當全天下都是瞎子嗎?啊?!」
「啊——!」建寧看到自己皇兄的御筆親繪被撕碎,像是被抽掉了最後一根主心骨,徹底瘋了。她哭喊著,廝打著,用所有她能想到的、最惡毒的語言咒罵著韋小寶。
房間裡頓時亂成了一鍋粥,下人們嚇得魂不附體,跪在地上瑟瑟發抖。欽差被夾在中間,臉上一陣青一陣白,恨不得自己當場瞎了聾了,或者直接昏死過去。
這場歸隱以來最激烈的爭吵,沒有贏家。只留下一地破碎的畫卷,兩個因為憤怒和絕望而面目全非的人,和一個被恐懼陰雲籠罩的家。
欽差眼看事情敗露到如此地步,早已嚇得三魂不見了七魄,找了個由頭,幾乎是連滾爬帶地逃出了韋府。他知道,自己無意中窺見了這個「皇親國戚」之家最可怕的秘密,這個秘密,足以要了他的命。
當天夜裡,韋小寶就倒下了。那場驚天動地的爭吵,徹底耗盡了他最後的一點元氣。
04
那場與建寧的激烈爭吵,像一陣狂風,不僅撕碎了康熙的畫,也徹底吹垮了韋小寶本就風雨飄搖的身體。
他病倒了,一病不起。
整日整日地躺在那張大床上,像是被釘在了上面。咳嗽變得越來越頻繁,也越來越重,有時候咳得撕心裂肺,會帶出血絲。請來的大夫換了一個又一個,從麗江本地的名醫,到蘇荃花重金從省城昆明請來的杏林國手,全都束手無策,開出的方子無非是些吊命的珍貴藥材。人參、靈芝、冬蟲夏草,像不要錢似的熬成湯藥,一碗碗地灌下去,卻也只能勉強維持著他那口氣不斷。
躺在床上,韋小寶的身體像一截被蟲蛀空了的朽木,但他的頭腦,卻在大多數時候異常地清醒。清醒得讓他痛苦。
關於韋虎和韋冬的疑雲,此刻在他心裡,已經不再是「懷疑」,而是板上釘釘的「事實」了。他覺得自己像個天底下最大的笑話,一個滑稽透頂的小丑。他為康熙皇帝賣了一輩子命,上刀山下火海,出生入死,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換來了這潑天的富貴和安逸。可到頭來呢?他最漂亮的夫人,給他戴了一頂綠油油的帽子,還可能讓他替頭號情敵養了二十年的兒子;他最尊貴的夫人,那個金枝玉葉的公主,更是膽大包天,直接讓他當了皇帝的「接盤俠」。
這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他韋小寶一輩子在女人堆里無往不利,自詡風流,沒想到老了老了,卻發現自己頭頂上綠草萋萋,都能跑馬了。
那股子羞辱感,像一把鈍刀,日日夜夜地在他心口上來回割,讓他不得安生。
他想起了自己的一生,從揚州麗春院裡一個任人打罵的小雜役,到今天這個富甲一方的韋老爺,靠的是什麼?是機靈,是會看人下菜碟,是懂得什麼時候該撒潑耍賴,什麼時候該裝孫子,什麼時候該挺身而出。說白了,就是懂得「裝糊塗」。可如今,他不想再糊塗下去了。他不能就這麼糊裡糊塗地死掉,變成一個糊塗鬼。
他咽不下這口氣。他不甘心。
他要證據,他要聽她們親口承認!
於是,他開始在病榻上,用他最後的力量,展開了一場無聲的調查。
他第一個找的,是他這一生最信任、最貼心的雙兒。在一個雙兒喂他喝藥的下午,他拉住雙兒的手,用微弱又沙啞的聲音對她說:「雙兒……我的好雙兒……你幫幫我……你去……你去聽聽,去看看……那些跟了阿珂和建寧多年的老媽子,她們一定知道些什麼。你賞她們金子,賞她們銀子,給她們的兒子家人安排好出路……只要她們肯說實話,要什麼都行。」
雙兒聽著他的話,眼淚撲簌簌地就掉下來了。她跪在床邊,把臉貼在他乾枯的手背上,哭得說不出話來。「相公,您別再想這些事了,好不好?再想下去,您的身子就真的垮了。孩子們……孩子們都是看著長大的,都是您的孩子,是咱們的孩子啊……」
她純粹的悲傷和不忍,像一盆冷水,澆在了韋小寶的心頭。他看著哭成淚人的雙兒,終究沒能狠下心來逼她。他知道,讓善良了一輩子的雙兒去做這種威逼利誘、探聽隱私的齷齪事,比殺了她還讓她難受。
雙兒這條路走不通,他又把主意打到了那些跟隨他多年的心腹管家身上。他把府里的大管家錢老本叫到床前。錢老本是他從揚州就帶出來的老人,對他忠心耿耿。
「老錢,」韋小寶喘著氣說,「我給你一千兩金子。你去辦件事。想辦法,撬開阿珂夫人和建寧公主院裡那幾個老人的嘴。我不要猜測,我要實打實的話。辦成了,我再給你兩千兩。」
錢老本「撲通」一聲跪在地上,老淚縱橫:「老爺!您這是要折殺老奴啊!老奴的命都是您給的,您讓老奴上刀山下油鍋,老奴眉頭都不皺一下。可是……可是這種事,老奴真的做不來啊!這後宅的事,是大夫人(蘇荃)在管,咱們……咱們插不上手啊!要是讓大夫人知道了,老奴死不足惜,只怕會攪得闔府不寧,反倒害了您的身子啊!」
韋小寶的心一點點地沉了下去。他慢慢地明白了。這個他親手建立起來的家,早就不完全是他的天下了。蘇荃,那個曾經的神龍教主夫人,用她超凡的智慧、手腕和威嚴,早已將這個後宅打理成了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鐵桶。在這個鐵桶里,女人們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維持這個家的「完整」和「體面」。
他,韋小寶,這個家的男主人,反而被她們聯手孤立了。他像一個坐在王座上的國王,卻發現自己的臣民們全都背著他達成了秘密的協議。
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無力感。
日子一天天過去,他的身體也一天天地衰敗下去。他開始整夜整夜地失眠,咳出來的血也從血絲變成了小口的血塊。他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對死亡的恐懼,像潮水一樣陣陣襲來,但比死亡更讓他恐懼的,是作為一個糊塗蛋死去的恥辱。
他必須知道真相。他不要再做一個明白鬼,他要在咽氣之前,就做一個明白人。
在一個深夜,韋小寶又經歷了一場劇烈的咳嗽,咳得他幾乎斷了氣。等他好不容易緩過一口氣來,他望著窗外那輪清冷孤高的月亮,渾濁的眼中,流露出一種令人心悸的、決絕的光芒。
他知道,用強的、用計的、用錢的,都沒用了。她們的聯盟堅不可摧。
他只剩下最後一樣武器了——他自己的「死」。
他要用自己彌留之際的最後一口氣,去撬開她們用幾十年光陰焊死的秘密。他要讓她們親口告訴他。這是一場賭局,他人生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場賭局,賭注是他一生的尊嚴。
「雙兒……」他用盡力氣,發出了微弱的呼喚。
一直在床邊椅子上打盹的雙兒猛地驚醒,連忙撲到床前,握住他的手:「相公,我在這裡,您怎麼了?」
「去……」韋小寶的嘴唇哆嗦著,每一個字都像是從牙縫裡擠出來的,「把她們……全都叫來。七個,一個……都不能少。告訴她們……就說我……我不行了……」
雙兒的心猛地一沉,她預感到了什麼。她看著韋小寶那張蒼白如紙,卻唯獨眼神亮得嚇人的臉,巨大的悲傷和恐懼攫住了她。但她知道,她無法違抗他,尤其是在這個時候。
她含著淚,重重地點了點頭:「是,相公。」
很快,韋小寶的臥房裡,燈火通明。七位夫人陸續到來,她們的腳步都很輕,仿佛怕驚擾了什麼。她們看著床上那個氣若遊絲,仿佛隨時都會咽氣的男人,每個人的臉上都帶著不同的複雜情緒——有悲傷,有恐懼,有憐憫,但更多的,是一種心照不宣的、深深的戒備。
一場最後的審判,即將開始。而審判者,卻是那個即將走向生命盡頭的人。
05
韋小寶的臥房裡,靜得能聽見燈芯在燈油里燃燒時發出的輕微「噼啪」聲,還有窗外偶爾傳來的幾聲蟲鳴。濃重的湯藥味混合著死亡的腐朽氣息,瀰漫在空氣中,壓得人喘不過氣。
七個女人,七個曾經攪動了他整個人生,與他命運緊緊糾纏在一起的女人,此刻都圍在了他的床邊。她們有的曾是他的敵人,有的曾是他的摯愛,有的曾是他強取豪奪的對象。如今,她們都是他的夫人,是他這個龐大家族的共同支柱。
韋小寶的胸口劇烈地起伏著,每一次呼吸都帶著沉重而嘶啞的風箱聲。他感覺自己的生命就像一個已經見底的沙漏,正在飛快地流逝著最後一縷沙。他必須抓緊時間。
他顫抖著,費力地伸出那隻枯瘦如柴、布滿青筋的手。
一直守在床邊的雙兒和站在最前面的蘇荃立刻上前,一左一右,握住了他冰冷的手。那隻曾經在皇宮裡偷雞摸狗,在賭場裡搖擲乾坤,在戰場上指點江山的手,如今瘦得只剩下皮包骨頭,輕飄飄的,毫無力氣。
他的目光,像一盞即將燃盡的油燈,吃力地、緩緩地掃過眼前的每一個女人。
他看到了蘇荃,她依舊端莊,但緊鎖的眉頭和緊抿的嘴唇泄露了她內心的緊張與決斷。他看到了雙兒,她眼中全是心碎與不忍,淚水在眼眶裡打轉,隨時都會落下。他看到了建寧,她站在稍遠的地方,眼神里充滿了怨恨和一絲不易察อก的躲閃,手指緊張地絞著衣角。他看到了阿珂,她站在人群的最後面,垂著頭,臉色蒼白得像一張紙,整個人仿佛是一尊沒有靈魂的玉像,散發著生人勿近的寒氣。他還看到了方怡、沐劍屏和曾柔,她們臉上交織著惶恐、茫然與不知所措。
她們的表情各不相同,卻又像一張無形的、堅韌的網,共同守護著一個他拼了命也想要觸碰到的中心。
韋小寶深吸一口氣,這一口氣仿佛抽乾了他全身最後殘存的力氣。
他的聲音很輕,很沙啞,卻像一把鋒利的錐子,一字一字地鑿進了在場每個人的心裡:
「我……我裝糊塗了大半生……你們……你們告訴我……」
他停頓了一下,積攢著力氣。他那雙渾濁的眼睛裡,突然迸發出一股令人心悸的光芒,那光芒里有憤怒,有不甘,有羞辱,但更多的,是一種近乎乞求的絕望。
「……哪幾個孩子……是我親生的?」
石破天驚。
整個房間的空氣,在這一句話問出口的瞬間,徹底凝固了。時間仿佛被凍結,萬籟俱寂,只剩下韋小寶那因為耗盡力氣而愈發粗重的喘息聲。
這句他已經在心裡反覆咀嚼、反覆吞咽了無數遍的話,終於還是像一顆燒紅的烙鐵,被他從滾燙的胸膛里掏了出來,狠狠地印在了這死寂的空氣中。它像一顆投入死水潭的巨石,激起了滔天的巨浪,將所有虛假的平靜和多年的偽裝撕得粉碎。
第一個做出反應的是雙兒。她的心理防線在這一刻徹底崩潰,眼淚瞬間決堤,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滾落下來,滴在韋小寶乾枯的手背上,滾燙得嚇人。
「相公!」她哭著喊道,聲音里充滿了無法言喻的痛苦,「您……您怎麼能這麼問!您要我們的心疼死嗎?我們的孩子……當然都是您的啊!您別胡思亂想了,相公!別想了!」
她的悲傷是如此純粹,如此真實,不帶任何雜質,像一把小刀,剜著在場每個人的心。
緊接著,建寧像是被踩了尾巴的潑婦貓,整個人都炸了起來,尖聲叫嚷道:「韋小寶!你都要死了還在這裡疑神疑鬼!本公主的孩子,龍子鳳孫,還能有假不成?你這是在咒我,還是在咒你自己?你安的什麼心!」
她的聲音又高又尖,帶著一種色厲內荏的虛張聲勢。她似乎覺得,只要自己的聲音足夠大,就能掩蓋住內心的恐懼和心虛,就能證明自己的清白。
而阿珂,她的反應最為劇烈,也最為安靜。在韋小寶問出那句話的瞬間,她的臉色「唰」地一下,變得慘白如紙,沒有一絲血色。
她的身體晃了一下,幾乎要站立不穩,幸好被身邊的曾柔扶了一把。她的嘴唇無聲地翕動了幾下,卻一個字也發不出來。她只是死死地攥住了自己的衣角,指節因為過度用力而發白。她垂下眼帘,長長的睫毛在燭光下投下一片濃重的陰影,整個人像一尊即將在下一秒無聲碎裂的玉像。她不敢看韋小寶,也不敢看任何人。
方怡和曾柔下意識地對視了一眼,都從對方眼中看到了同樣的驚慌失措。她們像是被突然捲入風暴中心的兩葉小舟,完全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沐劍屏更是嚇得小臉發白,她不懂這裡面複雜的糾葛,只是本能地感到害怕,怯生生地抓住曾柔的衣袖,小聲說:「小寶哥哥……你別嚇我們……大家……大家會害怕的……」
一片混亂中,只有蘇荃,還保持著最後的鎮定。
她眉頭緊鎖,臉色凝重。她先是安撫性地用力拍了拍韋小寶的手背,示意他冷靜,然後,她那雙經歷過大風大浪、依舊銳利如鷹的眼睛,像刀子一樣掃過房間裡亂作一團的姐妹們。
「都住口!」她沉聲喝道。
這一聲,分量十足,充滿了不容置喙的威嚴。建寧的尖叫戛然而止,雙兒的哭聲也小了下去。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集中在了她的身上,仿佛她才是這裡的主心骨。
蘇荃轉向韋小寶,神色複雜地看著他,語氣裡帶著一絲疲憊和沉重:「小寶,你這又是何苦。你這一輩子,有什麼天大的事,不是嘻嘻哈哈就混過去了?怎麼臨到頭了,非要鑽這個牛角尖。孩子們都是你的,是我們大家的孩子,這個家還在,這還不夠嗎?」
她的話,條理清晰,意有所指,像是在努力地把那個被韋小寶硬生生撕開的口子重新糊上。
但韋小寶不為所動。他知道,這是他最後的機會,一旦錯過,他將死不瞑目。他用盡全力,從喉嚨里擠出幾個字,那雙已經開始渙散的眼睛,卻越過蘇荃,死死地鎖在那個從頭到尾一言不發、如同雕像般的阿珂身上。
「阿珂……你先說。」
他的聲音微弱,卻帶著一股不得到答案絕不罷休的偏執和狠勁。
「虎兒……他……他到底是不是我的?」
整個房間,再一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落針可聞。
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探照燈一樣,齊刷刷地聚焦在了阿珂那張慘白如雪的臉上。她整個人都在無法控制地發抖,嘴唇哆嗦得厲害,似乎在與內心某種巨大的、折磨了她二十多年的力量進行著最後的抗爭。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空氣仿佛凝結成了冰,每一秒都像一年一樣漫長。
終於,阿珂像是下定了某種決心,又像是徹底放棄了抵抗。她緩緩地、極為艱難地抬起頭,迎向了韋小寶的目光。她的眼中沒有了之前的空洞和麻木,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令人心碎的、決絕的悲哀。她張開那早已沒有血色的嘴唇,似乎就要開口……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蘇荃突然上前一步,像一堵牆,穩穩地擋在了阿珂和韋小寶之間。
她的動作並不快,卻帶著一種斬釘截鐵、不容商量的決斷力。她對著床上那個即將油盡燈枯的男人,也像是對著在場的所有姐妹,一字一句地,清晰無比地說道:
「小寶,這件事,不是她們任何一個人的事。」
她頓了頓,環視了一圈眾人,加重了語氣:
「是我們七個姐妹,早就有了約定的事。」
她最後看向韋小寶,目光深沉如海:
「你何苦,非要再問?」
「約定?」
韋小寶的腦子「嗡」的一聲,幾乎停止了思考。什麼約定?她們之間……有什麼約定?他看著擋在自己面前,身形依舊挺拔、氣場強大的蘇荃,又越過她的肩膀,看向她身後那一張張神色各異、或驚恐、或悲傷、或麻木的臉。
他突然間明白了什麼。
這件事,遠比他想像的要複雜,要龐大。
這根本不是一個或者兩個女人的偶然背叛。
而是一個由他所有女人共同參與、共同保守了二十多年的,巨大的,深不見底的秘密。
這個秘密,到底是什麼?
蘇荃的話,像一扇剛剛被推開一絲縫隙的沉重鐵門,門縫裡透出的不是他渴求的光明,而是無盡的、令人窒息的黑暗。那個黑暗的深處,藏著他這個家的根基,也可能藏著足以將他徹底摧毀的真相。
06
「什麼……約定?」
韋小寶用盡全身的力氣,從喉嚨里擠出這幾個字。他的眼睛死死地盯著蘇荃,那雙渾濁的眼睛裡,寫滿了震驚、迷惑和一絲即將被真相吞噬的恐懼。他感覺自己像一個在黑暗中摸索了半輩子的人,馬上就要摸到那扇終極之門的門把手了。
蘇荃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似乎也在為接下來的話積攢勇氣。她轉過身,先是看了看臉色煞白的阿珂,又看了看一臉倔強卻同樣在發抖的建寧,最後,她的目光落在了哭得幾乎要暈厥過去的雙兒身上,眼神中閃過一絲憐憫和不忍。
她重新轉向韋小寶,聲音低沉而清晰,開始講述一個被塵封了將近二十年的往事。
「小寶,你還記不記得,咱們剛歸隱到麗江的第五個年頭。」蘇荃緩緩開口,她的聲音像是有魔力,讓整個房間的嘈雜和慌亂都平息了下來,「那一年,雲南大亂。一些不甘心的天地會舊部,勾結上了吳三桂的殘黨和地方上的土匪,在滇西一帶鬧得很大,燒殺搶掠,連官府都焦頭爛額。」
韋小寶的眼神有些迷茫,他在費力地回憶。那段日子,他確實不在家。他以為自己的身份早已洗白,可以高枕無憂,沒想到江湖上的恩怨還是找上了門。他不想讓朝廷插手,暴露自己的行蹤,只好親自出馬,帶著幾個從京城帶來的高手,去平息那場動亂。
蘇荃看著他的表情,知道他想起來了。她繼續說道:「你這一去,就是將近半年。剛開始還有消息斷斷續續傳來,後來,有兩個月的時間,你音訊全無。再後來……從外面傳來了消息,說你……說你中了亂黨的埋伏,已經……已經死在了哀牢山里。」
說到「死」字,雙兒的哭聲又忍不住大了起來,阿珂的身體也再次劇烈地顫抖了一下。那是韋家所有人都不願回憶的一段黑暗時光。
「你死了的消息傳回來,整個韋家大院,天都塌了。」蘇荃的眼神變得悠遠,仿佛又回到了那個風雨飄搖的時刻,「外面,那些亂黨和地方上的豪強,都像聞到血腥味的狼,盯著我們這家裡的萬貫家財,蠢蠢欲動。府里,下人們人心惶惶,一些手腳不幹凈的開始偷盜,一些有野心的管事開始拉幫結派,都想在你倒下後分一杯羹。我們這群女人,帶著一群半大的孩子,就像是待宰的羔羊。」
韋小寶靜靜地聽著,他從來不知道,在他看不到的地方,他的家,他的女人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危機。他一直以為她們在他的羽翼下,過得無憂無慮。
「那段時間,建寧整天哭著鬧著要回京城找皇兄,阿珂心灰意冷,把自己關在房裡不見任何人。方怡和曾柔她們也是六神無主,只有雙兒,一邊哭一邊還撐著,照顧孩子,安撫下人。」
「我看著這個即將分崩離析的家,我知道,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你不在了,我們要是再不擰成一股繩,不出三天,我們這群女人和孩子,就會被外面的豺狼虎豹吃得連骨頭渣子都不剩。」
蘇荃的眼中閃過一絲當年身為教主夫人時的狠厲和果決。
「於是,我把她們六個,全都叫到了我的房間裡。我關上門,跟她們進行了一次長談。我告訴她們,韋小寶是生是死,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們這群女人和這些孩子,要活下去。要想活下去,就不能再分彼此,不能再有私心。」
她的聲音變得莊嚴而肅穆,像是在宣讀一份神聖的誓言。
「就在那個晚上,我們七個姐妹,點上了香,對著關二爺的神像,立下了一個盟約。」
蘇荃看著韋小寶的眼睛,一字一句,清晰無比地說道:
「我們七個人對天發誓,從今往後,我們七姐妹榮辱與共,生死相依。這個家裡,就是我們共同的家。這個家裡所有的孩子,無論他的來處如何,無論他到底是誰的骨血,都只有一個爹,那就是韋小寶!他們都姓韋,都是韋家的子孫!我們七個人,就是所有孩子的娘!」
「盟約的最後一條是,誰要是敢向外人,包括向你韋小寶,泄露關於孩子身世的半個字,誰要是敢因為這些事挑起內鬥,破壞這個家,就叫她天打雷劈,五馬分屍,永世不得超生!」
這番話說完,整個房間陷入了更深沉的寂靜。建寧低下了頭,方怡和沐劍屏她們更是泣不成聲。這個當年為了自保而立下的惡毒誓言,像一道無形的枷鎖,捆綁了她們二十年。
韋小寶怔怔地聽著,心裡五味雜陳,像打翻了一整個調料鋪。他原以為,自己面對的是單純的姦情和背叛,他準備好去承受那份羞辱和憤怒。可他萬萬沒有想到,真相的背後,竟然是這樣一段為了生存而結下的、充滿了悲壯和無奈的女人之間的同盟。
他的憤怒,在這一刻,被一種更深沉、更複雜的悲哀所取代。他發現,在他看不到的地方,在他自以為是的掌控之外,他的女人們,也經歷了她們自己的「江湖」,她們的「刀光劍影」,甚至比他在外面經歷的更加兇險。
蘇荃沒有給他太多消化的時間,她知道,既然開了這個頭,就必須把話說完。
「阿珂,」她轉向阿珂,聲音放緩了一些,「當年,在你以為小寶已經死了,萬念俱灰的時候,鄭克塽輾轉找到了雲南來,想帶你走。你和他……有過一次會面。那時的你,孤苦無依,心神大亂,一時糊塗……」
她沒有把話說得太透,但意思已經再明白不過。
「還有建寧,」她又看向建寧,「你那次回京省親,正是小寶在外面為了平定神龍教餘孽的叛亂,長達一年沒有回家的時期。你們夫妻失和,你一個人在宮裡孤單寂寞,皇上……他對你這個唯一的妹妹多有撫慰,關心備至。深宮大內,皇家秘辛,孤男寡女,誰又能說得清那裡面的對與錯。」
蘇荃最後看著韋小寶,眼中滿是疲憊:「小寶,這些事,有的是發生在你『死』後,有的是發生在你對她們冷落疏遠之時。我們立下那個盟約,就是決定,把所有這些可能會毀了這個家的『過去』,全部埋葬。我們選擇集體沉默,共同撫養所有的孩子,把他們都當成是你的孩子來養大,只為了保護這個來之不易的、能讓我們所有人安身立命的家。」
「我們不是為了騙你一個人,」蘇荃的聲音裡帶著一絲顫抖,「我們是為了騙過所有人,騙過這個吃人的世道,甚至……騙過我們自己。只要我們自己信了,這個家,就還是完整的。」
07
蘇荃的話,像一陣沉重而悲涼的晚鐘,在韋小寶的耳邊久久迴響。
盟約。
原來如此。
他明白了為什麼這個家像個鐵桶,為什麼所有人都守口如瓶。原來,這不是一兩個人的背叛,而是一場由他所有女人共同參與的、為了生存而進行的「合謀」。
他的心裡,那股子沖天的怒火,被這悲涼的真相澆熄了大半,只剩下一點點不甘心的火星,和一片茫然的灰燼。他覺得自己像個在台下看戲的看客,一直以為台上演的是一出風流喜劇,到最後才發現,那其實是一出充滿了血淚和掙扎的悲劇,而他自己,既是戲裡的主角,又是唯一被蒙在鼓裡的傻子。
可是,他還是不甘心。
盟約是盟約,事實是事實。他已經沒有幾天好活了,他要聽的不是這個冠冕堂皇的「盟約」,他要的是那個最原始、最赤裸的「事實」。他要死得明明白白。
他掙扎著,從喉嚨里發出嗬嗬的聲音,眼睛死死地盯著蘇荃,又越過她,看向她身後的阿珂和建寧。他的眼神在說:我要聽她們親口說。
蘇荃讀懂了他的眼神。她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那口氣里,有疲憊,有解脫,也有一種宿命般的無奈。她知道,這個秘密守了二十年,終究還是到了要揭開的時候。也好,說開了,對所有人來說,或許都是一種解脫。
她默默地向後退了一步,讓開了位置,將舞台的中央,留給了那兩個秘密的核心。
所有的目光,再次聚焦在阿珂身上。
阿珂的身體抖得更厲害了。蘇荃的話,像是一把鑰匙,打開了她塵封了二十年的心牢。牢里關著的所有愧疚、悔恨、痛苦和恐懼,在這一刻奔涌而出,瞬間將她淹沒。
她再也支撐不住,雙腿一軟,「撲通」一聲,跪倒在韋小寶的床前,距離他不過幾尺之遙。
「我……我說……」她的聲音嘶啞得像被砂紙磨過,每一個字都帶著血淚,「我對不起你……」
她抬起頭,那張曾經絕美無雙的臉上,此刻布滿了淚痕,眼中是深不見底的絕望。「荃姐姐說的沒錯……那年,傳來你的死訊,我以為你真的死了。我覺得天都塌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就在那個時候,他……鄭克塽找到了我。」
「他說他後悔了,他說他這些年一直派人打探我的消息,他說他被流放關外,九死一生,心裡想的念的全是我。他說要帶我走,去一個沒人認識我們的地方,重新開始……我當時……我當時真的撐不住了……我覺得,既然你死了,我活著也沒什麼意思,不如就跟他走了……」
她泣不成聲,斷斷續續地說道:「就……就一次……就那麼一次……我便懷上了虎兒。可事後,我清醒過來,我就後悔了。我恨他,更恨我自己。我沒臉去見你,更沒臉活下去。是荃姐姐……是荃姐姐她們拉住了我,她們跟我說了那個盟約。她們說,為了孩子,為了虎兒能有一個堂堂正正的身份,而不是一個私生子,為了這個家不散,我必須把這個秘密爛在肚子裡。」
她一邊哭,一邊重重地對著韋小寶磕頭,額頭撞在冰冷的地板上,發出沉悶的響聲。
「我對不起你……韋小寶,我對不起你!但我……我更對不起虎兒!他這一輩子,都活在一個謊言里,他連自己的親生父親是誰,都不知道……」
阿珂的坦白,像一把尖刀,狠狠地扎進了韋小寶的心裡。雖然早已猜到,但親耳聽見,那種感覺還是不一樣。那是一種被證實了的、赤裸裸的羞辱。但他看著跪在地上,哭得幾乎要死過去的阿珂,心裡卻生不出一絲一毫的恨意,只剩下無盡的悲涼。
他沒有說話,只是轉動眼珠,將目光投向了另一個當事人——建寧公主。
建寧沒有跪。
她只是靜靜地站在那裡,臉上的囂張和乖張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深可見骨的疲憊和麻木。她迎著韋小寶的目光,沒有躲閃。
「看我做什麼?」她開口了,聲音很平靜,甚至帶著一絲自嘲的笑意,「你不是都猜到了嗎?」
她抬手,輕輕擦了擦眼角,說道:「沒錯,韋冬,他是皇兄的兒子。」
她的話,比阿珂的更直接,更不加掩飾。
「那次回宮,我感覺自己又活過來了。」她的眼神有些飄忽,像是在回憶遙遠的過去,「在雲南,我是你的老婆,是韋夫人,我要守你那一大家子的規矩,要看蘇荃的臉色。可是在紫禁城,我還是那個高高在上的建寧公主,皇兄……他對我很好,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好。他會陪我說話,陪我散步,聽我抱怨你的種種不是。他說我受委屈了。」
「那是一場心照不宣的錯誤。」她的臉上露出一個複雜的、說不清是甜蜜還是苦澀的笑容,「我不是為了背叛你,韋小寶。我只是……我只是想做回我自己。哪怕只有一次。我想找回那種被人捧在手心裡的感覺,找回做公主的感覺,而不是你韋小寶七個老婆里的一個。」
她說完,就沉默了,仿佛已經說完了她這輩子最想說的話。
阿珂和建寧的坦白,像推倒了第一塊多米諾骨牌。
方怡哭著上前一步,也跪了下來:「老爺,我……我雖然沒有做出越軌之事,但荃姐姐立下盟約的時候,我是同意的,我發了毒誓。我……我對不起您……」
曾柔和沐劍屏也跟著跪下,哭成一團。她們雖然天真單純,但也知道,守護這個秘密,本身就是對韋小寶的一種欺騙。
雙兒更是哭得肝腸寸斷。她一邊替韋小寶感到委屈和心痛,一邊又替這些命運多舛的姐妹感到悲哀。她撲在床邊,握著韋小寶的手,哽咽道:「相公……她們……她們也是沒辦法……您就……您就原諒她們吧……」
整個房間,充斥著女人們壓抑的哭聲和懺悔聲。
韋小寶得到了他想要的真相,一個又一個。這些真相像一把把雙刃劍,刺向了他,也狠狠地刺向了坦白的每一個人。他像是終於解開了一個困擾他一生的謎題,但看到謎底的那一刻,隨之而來的,卻是比謎題本身更加巨大的空虛、荒謬和悲涼。
他一生汲汲營營,費盡心機追求的「齊人之福」,他引以為傲的「妻妾成群,兒女滿堂」,原來,只是一個由謊言、秘密和女人的眼淚精心構建起來的、看似華美實則脆弱的空中樓閣。
而他,就是那個住在閣樓里,還自以為是天下最幸福的傻子。
08
知道了所有的真相之後,韋小寶陷入了長久的、死一般的沉默。
他不再說話,也不再看任何人。他就那麼睜著眼睛,空洞地望著頭頂上方的明黃色帳幔,那上面用金線繡著繁複的龍鳳呈祥圖案,此刻在他看來,充滿了無盡的諷刺。
房間裡的哭聲漸漸小了下去,只剩下壓抑的抽泣。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緊張地看著他。她們都在等待著,等待著他最後的審判。她們以為,他會爆發出最後的、雷霆萬鈞的憤怒,會用最惡毒的語言咒罵她們,然後在一場驚天動地的怨恨中死去。
畢竟,他是韋小寶。一個受了奇恥大辱的男人。
可是,他沒有。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久到仿佛連空氣都開始感到疲憊。
突然,韋小寶的嘴角,向上牽動了一下。他笑了。
那是一個極其古怪的笑容,比哭還難看,卻又帶著一絲說不清道不明的意味。他笑著,喉嚨里發出「嗬嗬」的聲音,隨即引發了一陣劇烈的咳嗽。
「咳咳……咳咳咳……」他咳得滿臉漲紅,幾乎要喘不上氣來。
「相公!」雙兒驚呼著,連忙替他撫背順氣。
好半天,韋小寶才緩了過來。他無力地擺了擺手,示意跪了一地的女人們都起來。他的聲音,比之前任何時候都要微弱,卻也平靜得不可思議。
「都……都起來吧……跪著做什麼……地上涼……」
女人們將信將疑地站起身,面面相覷,都不知道他這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藥。
韋小寶的目光,緩緩地從她們身上移開,投向了被這邊的動靜驚動,正站在門口,一臉驚惶和不知所措的韋虎和韋冬。
「虎兒……冬兒……過來……」他朝他們招了招手。
韋虎和韋冬對視一眼,猶豫著走了進來。他們的臉色都很蒼白,顯然,剛才房裡的對話,他們已經聽到了大半。這對他們來說,不啻於天塌地陷。
兩人走到床前,默默地跪下,低著頭,不敢看韋小寶。
韋小寶伸出那隻已經沒有多少溫度的手,先是摸了摸韋虎的頭。韋虎渾身一僵。
「好小子……」韋小寶的聲音很輕,「長得……長得真俊……像你……像你娘……」
他的話里,沒有一絲一毫的怨恨和責備,反而像一個普通的、行將就木的父親,對自己孩子最質樸的誇讚。韋虎的肩膀劇烈地顫抖起來,他把頭埋得更低了,滾燙的淚水砸在了地板上。
然後,韋小寶又把手轉向韋冬,吃力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你這孩子,有出息……像……像個做大事的人……」他喘了口氣,繼續說道,「以後……以後我不在了……你和你大哥……要撐起這個家……要照顧好你們的娘……和……和弟弟妹妹們……」
他對他們,沒有一句質問,沒有一句責備,反而像一個最尋常的父親一樣,平靜地交代著後事。
在場的所有人,都怔住了。她們不懂,韋小寶為什麼不生氣,為什麼不憤怒。
只有蘇荃,看著韋小寶那雙已經開始渙散的眼睛,似乎隱隱明白了一些什麼。
韋小寶又把目光轉回到他的女人們身上。他再次費力地伸出雙手,蘇荃和雙兒再次握住。他攥著她們的手,目光一個一個地看過去,像是要把她們的模樣,刻進自己的靈魂里。
最後,他那幾乎已經沒有焦距的眼睛,看著帳幔,斷斷續續地,像是對自己說,又像是對所有人說:
「親生的……不親生的……又……又能怎麼樣呢……」
「養了……養了這麼多年……有哭……有笑……有吵……有鬧……」
「在我韋家的屋檐下長大……吃我韋家的飯……叫我一聲爹……那……就都是我的種……」
他似乎是想笑一下,卻已經沒有力氣了。
「挺好……這樣……挺好……」
他的目光,最後轉向了一直握著他手的蘇荃,輕輕地點了點頭。那一個點頭,包含了太多複雜的情緒。有埋怨,有諒解,但更多的,似乎似乎是一種遲來的感謝。感謝她,用她的鐵腕和智慧,維繫住了這個看似荒唐卻又無比真實的「家」。
然後,他用盡最後一絲力氣,轉過頭,看向了他生命中唯一的、也是永遠的港灣——雙兒。
雙兒正滿臉淚水地看著他,眼中是無盡的眷戀和心痛。
韋小寶的嘴唇動了動,他想對她說句什麼。或許是想說一句「對不起」,因為他知道,在這所有的妻妾里,唯有雙兒,對他奉獻了全部的、毫無保留的愛與忠誠,而他,卻帶給了她這樣一個充滿了欺騙和秘密的家庭。又或許是想說一句「謝謝你」,謝謝她一輩子的陪伴和不離不棄。
可是,他終究什麼也沒能說出口。他的喉嚨里發出了一聲輕微的、像是嘆息一樣的聲響,然後,他的身體徹底放鬆了下來,那雙一直努力睜著的眼睛,緩緩地、永遠地閉上了。
那隻緊緊攥著雙兒和蘇荃的手,也隨之失去了最後的力氣,無力地滑落。
「相公——!」
雙兒發出一聲悽厲的哭喊,撲倒在韋小寶的身上,痛不欲生。
整個房間,瞬間被巨大的、無法抑制的哭聲所淹沒。阿珂跪在地上,哭得渾身抽搐;建寧捂著臉,發出了壓抑而痛苦的嗚咽;方怡、曾柔、沐劍屏相擁而泣。韋虎和韋冬跪在床前,額頭抵地,肩膀劇烈地聳動著。
這個攪動了大清半個世紀風雲,從揚州的地痞流氓,一路奇遇,做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鹿鼎公韋小寶,就這麼走了。
他裝糊塗過了一生,臨死前,偏執地求一個明白。
可當他真的得到了這個「明白」之後,才發現,原來「糊塗」才是他這一生最大的福氣。
他一直以為,他用自己的權勢、金錢和手段,征服了這些女人,擁有了她們。可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才恍然大悟,不是他擁有了她們,而是她們所有人,用各自的犧牲、隱忍和謊言,共同「擁有」了他所構建的這個可以遮風避雨的家。
這個家,雖然根基建立在謊言之上,但幾十年的朝夕相處,幾十年的吵吵鬧鬧,幾十年的互相扶持,那份早已滲透進骨血里的親情和羈絆,早已比那虛無縹緲的血緣,更加堅韌,更加真實。
親生的,不親生的,又如何呢?
他韋小寶,終究還是做了一回「明白鬼」。而這個明白,沒有帶給他怨恨,只帶給了他最後的、荒誕的平靜。
或許,對他來說,這便是最好的結局。
韋小寶的喪事,辦得極其隆重,甚至有些鋪張。整個麗江城,但凡有頭有臉的人物都前來弔唁。出殯那天,送葬的隊伍從韋府門口一直排出去了好幾里地。
喪事由蘇荃一手操持,辦得井井有條,滴水不漏,讓所有人都見識到了這位韋家大夫人的手腕和威儀。
靈堂設在正廳,正中懸掛著韋小寶的畫像。畫像上的他,還是中年時的模樣,穿著一品大員的朝服,臉上帶著那標誌性的、似笑非笑的表情,眼神里透著一股子機靈和狡黠,仿佛隨時都會從畫里跳出來,說一句:「奶奶的,哭什麼哭,老子還沒死透呢!」
韋豹、韋虎、韋冬等幾個兒子,身穿重孝,跪在靈前,為前來弔唁的賓客一一還禮。他們的臉上都帶著悲傷,但神情卻很平靜。
尤其是韋虎和韋冬,在經歷了那一夜的天崩地裂之後,他們仿佛一夜之間長大了。他們看彼此的眼神,沒有了往日的競爭和隔閡,反而多了一種同病相憐、相依為命的默契。
七位夫人一身素服,站在靈堂的側面。她們的眼睛都哭得紅腫,但沒有一個人失態。她們只是靜靜地站著,像七座沉默的雕像,共同送別那個讓她們又愛又恨了一輩子的男人。
喪事過後,生活似乎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但所有人都知道,有些東西,已經永遠地改變了。
一天下午,陽光正好。
蘇荃處理完府中的帳目,感到有些疲憊,便一個人來到後花園的涼亭里歇息。雙兒端著一碗剛燉好的燕窩,悄悄走了過來。
「荃姐姐,累了吧,喝點東西潤潤喉。」
蘇荃接過燕窩,卻沒有喝,只是用勺子輕輕攪動著。她看著滿園在陽光下盛開的花朵,輕聲問道:「雙兒,你……你怪我嗎?」
雙兒愣了一下,隨即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搖了搖頭,在蘇荃身邊坐下,柔聲說:「不怪。我知道,姐姐這麼做,都是為了這個家,為了我們大家。」她頓了頓,眼中泛起淚光,「我只是……只是心疼相公。他這一輩子,活得太累了。」
蘇含聞言,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眼中也流露出一絲悲戚:「是啊,他活得累,我們又何嘗不累呢?守著一個天大的秘密,守了幾十年,日日夜夜,如履薄冰。現在,他走了,我們……也算是解脫了。」
兩人沉默了片刻。
「那天晚上,」雙兒輕聲問,「相公他最後……是不是明白了什麼?」
蘇荃抬起頭,看向不遠處。韋虎和韋冬正並肩走在小徑上,不知在說些什麼。韋虎還是那般俊朗,但眉宇間多了幾分沉穩;韋冬還是那般氣度不凡,但眼神里卻少了幾分疏離,多了一絲屬於這個家的溫情。
蘇荃的臉上,露出了一個極其複雜的、混雜著欣慰與悲涼的笑容。
她緩緩地,卻又無比篤定地說道:「他明白了。」
「他最後,是明白了。糊塗了一輩子,臨死前,他終於做了一回真正的明白人。他明白,這個家,就是他的家。這些孩子,就是他的孩子。血緣……有時候,並沒有那麼重要。」
陽光穿過亭子的飛檐,在青石地面上投下斑駁的光影。遠處的草場上,又傳來了孩子們的嬉笑聲和打鬧聲。新一代的韋家子孫,正在無憂無慮地成長。
韋家大院,依舊是那個富麗堂皇、人丁興旺的韋家大院。
生活,還要繼續。
只是那個給這個家帶來了一切財富與榮耀,也帶來了一切紛爭與秘密的男人,已經永遠地睡著了。
在他走後,這個由謊言維繫的家,反而因為真相的揭開,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堅固。因為所有人都知道,他們如今所擁有的一切,都是用那個男人的妥協,和她們所有人的青春、眼淚與秘密,共同換來的。
他們,再也分不開了。
 呂純弘 • 133K次觀看
呂純弘 • 133K次觀看 呂純弘 • 12K次觀看
呂純弘 • 12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花峰婉 • 17K次觀看
花峰婉 • 17K次觀看 呂純弘 • 10K次觀看
呂純弘 • 10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9K次觀看
呂純弘 • 9K次觀看 奚芝厚 • 9K次觀看
奚芝厚 • 9K次觀看 呂純弘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滿素荷 • 4K次觀看
滿素荷 • 4K次觀看 喬峰傳 • 34K次觀看
喬峰傳 • 34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24K次觀看
呂純弘 • 2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9K次觀看
呂純弘 • 49K次觀看 幸山輪 • 22K次觀看
幸山輪 • 22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