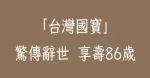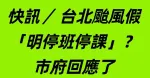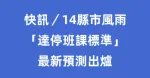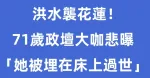2/3
下一頁
臨終前韋小寶攥著幾位夫人的手問:告訴我,哪個孩子是我親生的

2/3
韋小寶在她對面的椅子上費力地坐下,喘了口氣,臉上習慣性地掛起他那標誌性的嬉皮笑臉:「沒什麼,沒什麼,就是人老了睡不著,到處溜達溜達。唉,人一老啊,就愛想以前的事兒。」
他頓了頓,眼睛看似隨意地在屋裡掃了一圈,最終落在她身上,然後仿佛是忽然想起什麼似的,不經意地開口:「說起來啊……也不知道當年在台灣那個姓鄭的小白臉,後來到底怎麼樣了。我記得後來聽人說,被小玄子……呃,被皇上發配到關外最北邊那個苦寒地兒去了,你說,他是不是早就凍死在那兒,投胎做豬做狗去了?」
他的話音剛落,屋子裡的空氣像是瞬間凝固了,連窗外竹葉的沙沙聲都聽不見了。
阿珂正在給一盆名貴的墨蘭澆水的手,猛地頓了一下。她沒有回頭,依然背對著韋小寶,但她那微微繃緊的、線條優美的脊背,已經泄露了她內心的不平靜。
過了好一會兒,長得仿佛有一個世紀那麼久,她才重新拿起小巧的紫砂水壺,繼續那未完的動作,細細的水流澆在蘭花的根部。她的聲音像院子裡的井水一樣清冷,聽不出半分喜怒:「老爺說這些陳年舊事做什麼,不過是些無關緊要的人,提他作甚,沒的污了耳朵。」
這反應,在疑心已經重到快要爆炸的韋小寶看來,無異於心虛。要是真的毫不在意,以她剛烈的性子,要麼就痛罵鄭克塽一頓解恨,要麼就乾脆付之一笑,當個屁給放了。這種不願提及、刻意迴避的態度,恰恰說明她心裡有鬼!她還念著那個小白臉!
韋小寶心裡的那股邪火「蹭」地一下就頂到了腦門。他幾乎要控制不住地拍案而起,指著她的鼻子質問她跟鄭克塽到底有沒有私情,但話到嘴邊,又被他硬生生地咽了下去。
不行。不能這麼問。這麼問,她肯定打死都不會承認。老子要的是真相,不是圖一時痛快跟她吵架。
他強行壓下翻騰的怒火,臉上擠出兩聲乾笑:「呵呵,是是是,夫人說的是,不提了,不提了。都是些過去的事了嘛,不值一提。我就是年紀大了,嘴碎,隨便說說,隨便說說。」
他裝模作樣地站起身,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往外走。在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忽然像想起了什麼,猛地回頭,用一種半開玩笑的口吻補了一句:「對了,咱們家虎兒這孩子,長得是真俊,英氣逼人,就是……越來越不像我這個當爹的了,哈哈……」
這一次,阿珂連澆水的動作都沒停,只是聲音比剛才更冷了一分:「孩子長大了,自然有他自己的模樣,有什麼好奇怪的。」
韋小寶的笑容徹底僵在了臉上。他知道,再也問不出什麼了。阿珂就像一塊捂不熱的寒冰,他所有的試探和心機,在她面前都像打在了棉花上,軟綿綿的,不起半點作用。
他拄著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出了阿珂的院子。來的時候心裡憋著一股勁兒,回去的時候,那股勁兒全泄了,只剩下滿心的悲涼和屈辱。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自己的心上,又沉又痛。他覺得自己就像個上躥下跳的小丑,試圖去揭開一個可能讓他顏面掃地的秘密,結果卻被對方輕描淡寫地擋了回來,還碰了一鼻子灰。
這讓他更加堅信了自己的猜測。阿珂的平靜,在他看來,就是最大的不平靜。
這天下午,韋府里發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阿珂把韋虎叫到了自己的房裡,關上門,不知說了些什麼。小半個時辰後,韋虎出來時,一向神采飛揚的臉上滿是壓抑,眼圈也是紅的,像是大哭過一場。從那天起,一向有些張揚跳脫的韋虎,忽然變得沉默寡言起來,見到韋小寶,眼神也有些躲閃,不再像以前那樣親熱地湊上來。
這一切,韋小寶都通過安插在各院的眼線,看得一清二楚,記在心裡。他沒有聲張,但那根扎在他心裡的毒針,又被狠狠地往深處戳進了一寸,疼得他夜裡都睡不著覺。
03
關於韋虎的疑雲尚未散去,另一場更大的風暴,已經悄無聲息地從千里之外的京城席捲而來,直撲韋家大院。
阿珂那件事,對韋小寶的打擊極大。他本就衰老的身體,被這股子心火一攻,徹底垮了。他整日躺在床上,湯藥不斷,咳嗽得愈發厲害,常常咳得滿臉通紅,上氣不接下氣,精神也一天比一天萎靡不振。
就在這時,京城來了欽差,說是奉了皇上的旨意,聽聞桂貝勒身體抱恙,特命人送來關懷,並探望遠在雲南的「和碩恪靖公主」,也就是建寧。
這在韋家是天大的事。全府上下立刻忙碌起來,洒掃庭院,張燈結彩,準備迎接聖使。
韋小寶拖著一副病體,也得在雙兒和蘇荃的攙扶下,強打精神出來見見欽差。畢竟,這是小玄子派來的人,這個面子不能不給。
欽差是個面孔圓滑、見風使舵的中年官員,見了韋小寶,滿臉堆笑,一口一個「桂貝勒」,姿態放得極低,恭敬得不得了。一番客套寒暄過後,便是宣讀聖旨,無非是些勉勵和安撫的話,然後開始賞賜禮物。
賞給韋家的東西,從關外的千年老參、東海的上品珍珠,到江南的極品絲綢、景德鎮的官窯瓷器,裝了滿滿十幾大箱,極盡奢華,晃得人眼花。
但這些,韋小寶都沒怎麼放在心上。他這輩子,什麼寶貝沒見過?皇宮大內里的稀世珍寶他都當彈珠玩過。
他真正有點在意的,是欽差宣旨完畢後,單獨捧出來,鄭重其事地交給建寧公主的一個長條形的紫檀木錦盒。
「公主千歲,」欽差躬著身子,笑得像朵菊花,「這是皇上聽聞您在麗江一切安好,龍心大悅,特地熬了好幾個通宵,親筆為您畫的一幅畫,以慰您的思鄉之情。」
建寧一聽是皇兄的御筆親繪,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像天上最亮的星星。她歸隱二十多年,刁蠻的脾氣雖然被歲月和蘇荃的管束收斂了不少,但骨子裡那份與生俱來的皇家驕傲和對紫禁城繁華生活的無盡念想,從未有半刻斷絕過。
她迫不及待地接過錦盒,打開來,取出一卷用明黃色絲綢包裹的畫軸,小心翼翼地,帶著朝聖般的虔誠,緩緩展開。
畫上,是一個眉眼精緻的華服少年,在一片空曠的廣場上,獨自放著一隻繪著鳳凰圖案的精美風箏。在他的身後,是層層疊疊的宮殿,金瓦紅牆,氣勢恢宏,一眼便知是那座睏了她半輩子的紫禁城。
畫的右上角,有一行飄逸瀟洒的題字,筆力遒勁:遙念皇妹,憶及幼時嬉戲光景,特繪此圖,以慰思鄉之情。落款是康熙的私印。
建寧看著畫,只是那麼一眼,眼圈就一下子紅了。她伸出手指,輕輕地、愛惜地撫摸著畫上少年那張俊秀的臉,口中喃喃自語,聲音哽咽:「皇兄……皇兄他還記得我……他還記得……」
韋小寶也被雙兒扶著,湊過去看。初看時,只覺得這畫畫得是真好,那宮牆,那殿宇,那漢白玉的欄杆,跟他記憶里的乾清宮一模一樣。可當他的目光,慢慢地落在那畫中少年的臉上時,他的呼吸猛地一窒。
這畫中少年……怎麼這麼眼熟?
他皺起眉頭,死死地盯著那張臉,仔細端詳。那挺直的鼻樑,那薄薄的卻緊抿著的嘴唇,尤其是嘴角那倔強地上揚的弧度,還有那雙看似平靜淡然、實則深處藏著一股子睥睨天下之傲氣的眼睛……
這不是……這不是他媽的韋冬嗎?!
他頓了頓,眼睛看似隨意地在屋裡掃了一圈,最終落在她身上,然後仿佛是忽然想起什麼似的,不經意地開口:「說起來啊……也不知道當年在台灣那個姓鄭的小白臉,後來到底怎麼樣了。我記得後來聽人說,被小玄子……呃,被皇上發配到關外最北邊那個苦寒地兒去了,你說,他是不是早就凍死在那兒,投胎做豬做狗去了?」
他的話音剛落,屋子裡的空氣像是瞬間凝固了,連窗外竹葉的沙沙聲都聽不見了。
阿珂正在給一盆名貴的墨蘭澆水的手,猛地頓了一下。她沒有回頭,依然背對著韋小寶,但她那微微繃緊的、線條優美的脊背,已經泄露了她內心的不平靜。
過了好一會兒,長得仿佛有一個世紀那麼久,她才重新拿起小巧的紫砂水壺,繼續那未完的動作,細細的水流澆在蘭花的根部。她的聲音像院子裡的井水一樣清冷,聽不出半分喜怒:「老爺說這些陳年舊事做什麼,不過是些無關緊要的人,提他作甚,沒的污了耳朵。」
這反應,在疑心已經重到快要爆炸的韋小寶看來,無異於心虛。要是真的毫不在意,以她剛烈的性子,要麼就痛罵鄭克塽一頓解恨,要麼就乾脆付之一笑,當個屁給放了。這種不願提及、刻意迴避的態度,恰恰說明她心裡有鬼!她還念著那個小白臉!
韋小寶心裡的那股邪火「蹭」地一下就頂到了腦門。他幾乎要控制不住地拍案而起,指著她的鼻子質問她跟鄭克塽到底有沒有私情,但話到嘴邊,又被他硬生生地咽了下去。
不行。不能這麼問。這麼問,她肯定打死都不會承認。老子要的是真相,不是圖一時痛快跟她吵架。
他強行壓下翻騰的怒火,臉上擠出兩聲乾笑:「呵呵,是是是,夫人說的是,不提了,不提了。都是些過去的事了嘛,不值一提。我就是年紀大了,嘴碎,隨便說說,隨便說說。」
他裝模作樣地站起身,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往外走。在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忽然像想起了什麼,猛地回頭,用一種半開玩笑的口吻補了一句:「對了,咱們家虎兒這孩子,長得是真俊,英氣逼人,就是……越來越不像我這個當爹的了,哈哈……」
這一次,阿珂連澆水的動作都沒停,只是聲音比剛才更冷了一分:「孩子長大了,自然有他自己的模樣,有什麼好奇怪的。」
韋小寶的笑容徹底僵在了臉上。他知道,再也問不出什麼了。阿珂就像一塊捂不熱的寒冰,他所有的試探和心機,在她面前都像打在了棉花上,軟綿綿的,不起半點作用。
他拄著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出了阿珂的院子。來的時候心裡憋著一股勁兒,回去的時候,那股勁兒全泄了,只剩下滿心的悲涼和屈辱。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自己的心上,又沉又痛。他覺得自己就像個上躥下跳的小丑,試圖去揭開一個可能讓他顏面掃地的秘密,結果卻被對方輕描淡寫地擋了回來,還碰了一鼻子灰。
這讓他更加堅信了自己的猜測。阿珂的平靜,在他看來,就是最大的不平靜。
這天下午,韋府里發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阿珂把韋虎叫到了自己的房裡,關上門,不知說了些什麼。小半個時辰後,韋虎出來時,一向神采飛揚的臉上滿是壓抑,眼圈也是紅的,像是大哭過一場。從那天起,一向有些張揚跳脫的韋虎,忽然變得沉默寡言起來,見到韋小寶,眼神也有些躲閃,不再像以前那樣親熱地湊上來。
這一切,韋小寶都通過安插在各院的眼線,看得一清二楚,記在心裡。他沒有聲張,但那根扎在他心裡的毒針,又被狠狠地往深處戳進了一寸,疼得他夜裡都睡不著覺。
03
關於韋虎的疑雲尚未散去,另一場更大的風暴,已經悄無聲息地從千里之外的京城席捲而來,直撲韋家大院。
阿珂那件事,對韋小寶的打擊極大。他本就衰老的身體,被這股子心火一攻,徹底垮了。他整日躺在床上,湯藥不斷,咳嗽得愈發厲害,常常咳得滿臉通紅,上氣不接下氣,精神也一天比一天萎靡不振。
就在這時,京城來了欽差,說是奉了皇上的旨意,聽聞桂貝勒身體抱恙,特命人送來關懷,並探望遠在雲南的「和碩恪靖公主」,也就是建寧。
這在韋家是天大的事。全府上下立刻忙碌起來,洒掃庭院,張燈結彩,準備迎接聖使。
韋小寶拖著一副病體,也得在雙兒和蘇荃的攙扶下,強打精神出來見見欽差。畢竟,這是小玄子派來的人,這個面子不能不給。
欽差是個面孔圓滑、見風使舵的中年官員,見了韋小寶,滿臉堆笑,一口一個「桂貝勒」,姿態放得極低,恭敬得不得了。一番客套寒暄過後,便是宣讀聖旨,無非是些勉勵和安撫的話,然後開始賞賜禮物。
賞給韋家的東西,從關外的千年老參、東海的上品珍珠,到江南的極品絲綢、景德鎮的官窯瓷器,裝了滿滿十幾大箱,極盡奢華,晃得人眼花。
但這些,韋小寶都沒怎麼放在心上。他這輩子,什麼寶貝沒見過?皇宮大內里的稀世珍寶他都當彈珠玩過。
他真正有點在意的,是欽差宣旨完畢後,單獨捧出來,鄭重其事地交給建寧公主的一個長條形的紫檀木錦盒。
「公主千歲,」欽差躬著身子,笑得像朵菊花,「這是皇上聽聞您在麗江一切安好,龍心大悅,特地熬了好幾個通宵,親筆為您畫的一幅畫,以慰您的思鄉之情。」
建寧一聽是皇兄的御筆親繪,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像天上最亮的星星。她歸隱二十多年,刁蠻的脾氣雖然被歲月和蘇荃的管束收斂了不少,但骨子裡那份與生俱來的皇家驕傲和對紫禁城繁華生活的無盡念想,從未有半刻斷絕過。
她迫不及待地接過錦盒,打開來,取出一卷用明黃色絲綢包裹的畫軸,小心翼翼地,帶著朝聖般的虔誠,緩緩展開。
畫上,是一個眉眼精緻的華服少年,在一片空曠的廣場上,獨自放著一隻繪著鳳凰圖案的精美風箏。在他的身後,是層層疊疊的宮殿,金瓦紅牆,氣勢恢宏,一眼便知是那座睏了她半輩子的紫禁城。
畫的右上角,有一行飄逸瀟洒的題字,筆力遒勁:遙念皇妹,憶及幼時嬉戲光景,特繪此圖,以慰思鄉之情。落款是康熙的私印。
建寧看著畫,只是那麼一眼,眼圈就一下子紅了。她伸出手指,輕輕地、愛惜地撫摸著畫上少年那張俊秀的臉,口中喃喃自語,聲音哽咽:「皇兄……皇兄他還記得我……他還記得……」
韋小寶也被雙兒扶著,湊過去看。初看時,只覺得這畫畫得是真好,那宮牆,那殿宇,那漢白玉的欄杆,跟他記憶里的乾清宮一模一樣。可當他的目光,慢慢地落在那畫中少年的臉上時,他的呼吸猛地一窒。
這畫中少年……怎麼這麼眼熟?
他皺起眉頭,死死地盯著那張臉,仔細端詳。那挺直的鼻樑,那薄薄的卻緊抿著的嘴唇,尤其是嘴角那倔強地上揚的弧度,還有那雙看似平靜淡然、實則深處藏著一股子睥睨天下之傲氣的眼睛……
這不是……這不是他媽的韋冬嗎?!
 呂純弘 • 133K次觀看
呂純弘 • 133K次觀看 呂純弘 • 12K次觀看
呂純弘 • 12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花峰婉 • 17K次觀看
花峰婉 • 17K次觀看 呂純弘 • 10K次觀看
呂純弘 • 10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9K次觀看
呂純弘 • 9K次觀看 奚芝厚 • 9K次觀看
奚芝厚 • 9K次觀看 呂純弘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滿素荷 • 4K次觀看
滿素荷 • 4K次觀看 喬峰傳 • 34K次觀看
喬峰傳 • 34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24K次觀看
呂純弘 • 2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9K次觀看
呂純弘 • 49K次觀看 幸山輪 • 22K次觀看
幸山輪 • 22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