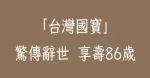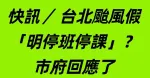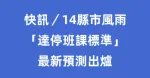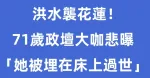1/3
下一頁
臨終前韋小寶攥著幾位夫人的手問:告訴我,哪個孩子是我親生的

1/3
臨終前韋小寶攥著幾位夫人的手問:告訴我,哪個孩子是我親生的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本文所用素材源於網際網路,部分圖片非真實圖像,僅用於敘事呈現,請知悉
在雲南麗江的暖陽下,曾經攪動天下風雲的鹿鼎公韋小寶,已是行將就木的古稀老人。
他坐擁著潑天富貴,享受著七位夫人和滿堂兒孫的環繞,這份看似圓滿的天倫之樂,本應是他傳奇一生最安詳的句點。
這份平靜之下,懷疑的陰影卻早已如毒藤般悄然滋生,纏繞住他日漸衰竭的心脈。
他審視著一張張熟悉又陌生的子孫面孔,那些不經意間流露出的、與自己迥異的神態和氣度,像一根根尖刺,扎在他裝糊塗了大半生的面具上,讓他覺得自己像一個天大的笑話。
當生命的燈火即將燃盡,他用盡最後一口氣,將七位夫人悉數叫到床前。
在昏暗的燭光與女人們複雜的目光中,這個一生都在嬉笑怒罵中求生的男人,攥緊了她們的手,問出了那個足以摧毀一切的、顫抖著的問題……
01
雲南,麗江。
這座遠離了京城喧囂的古城,用它特有的慵懶和溫吞,將一個曾經攪動了大清王朝風雲的男人,打磨成了一個安詳富足的古稀老人。
韋家的府邸,是整個麗江城裡最氣派的所在。三進三出的大院子,亭台樓閣,雕樑畫棟,後院引了玉龍雪山的活水,繞著假山潺潺流淌,養著從江南運來的名貴錦鯉。
府里的下人,從管家到燒火的丫頭,都知道韋老爺富可敵國,當年是隨著聖駕平定吳三桂的大功臣,封過一等鹿鼎公,連當今皇上,都得尊稱他一聲「桂貝勒」,私下裡或許還會親昵地叫一聲「小桂子」。
可這些輝煌,都已經是陳芝麻爛穀子的舊事了。如今的韋小寶,更像個尋常的富家翁,一個被歲月和舊傷徹底掏空了精氣神的老頭兒。他的背駝了,頭髮白得像玉龍山的雪,臉上布滿了老年斑,走幾步路就要喘上半天。
清晨的陽光透過精緻的雕花窗欞,斑駁地灑在紫檀木的拔步大床上。韋小寶在一陣撕心裂肺的咳嗽聲中醒來,咳得整個人都蜷縮成了蝦米,感覺肺葉子都要從喉嚨里翻出來了。守在床邊的雙兒立刻端上溫熱的蜜水,用那雙幾十年如一日溫柔的手,輕輕拍著他的後背。
「相公,慢點兒,順順氣。」她的聲音還是那麼軟糯,像是能撫平世間一切的焦躁。
韋小寶喝了水,喉嚨里那股子鐵鏽般的腥甜感才稍稍壓下去一些。他靠在幾個厚實的雲錦枕頭上,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一雙曾經精光四射的眼睛如今變得渾濁不堪,望著窗外。院子裡的三角梅開得潑辣又張揚,像一團燒得正旺的火。可他只覺得身上發冷,那股子從骨頭縫裡絲絲縷縷透出來的寒意,是再厚的狐皮被子也捂不熱的。
「雙兒,扶我出去走走。」他的聲音沙啞得厲害。
「哎,」雙兒應著,手腳麻利地取來一件織錦鑲白狐毛的披風給他仔細穿上,「大夫囑咐了,您這老寒腿最怕見風。咱們就在廊下坐坐,曬曬太陽,暖和暖和身子,好不好?」
韋小寶沒力氣爭辯,哼唧了一聲,算是默許了。
雙兒的力氣比年輕時小多了,但依舊是他最穩固的依靠。她幾乎是半抱著,才將他那副乾癟的身體挪到了院中廊下的紫藤蘿躺椅上。陽光照在臉上,暖洋洋的,他舒服地眯起了眼睛。幾個年紀小點的孫子孫女像一群小麻雀,嘰嘰喳喳地跑過來,圍著他「爺爺、爺爺」地叫個不停,把剝好的橘子瓣兒往他嘴裡塞。
韋小寶臉上擠出一絲皺巴巴的笑容,從懷裡摸出幾塊早就準備好的麥芽糖,顫巍巍地遞給他們。「吃吧,吃吧,都是好孩子,都長高了……」
他看著這滿院的兒孫,大的已經娶妻生子,在外面獨當一面;小的還在咿呀學語,繞著他的腿打轉。一張張鮮活的面孔,本該是他韋小寶這一生最得意、最值得吹噓的成就。可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看他們的眼神變了。那種發自內心的、天倫之樂的欣慰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近乎審視的、帶著探究的陌生目光。
他這一輩子,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紫禁城裡跟小玄子摔跤打鬧,天地會裡當香主指點江山,神龍島上做白龍使虛與委蛇。他靠的是什麼?不是那一身不入流的武功,更不是那斗大的字認不了一籮筐的學問。
他靠的,是他那顆比誰都轉得快的腦子,是那一肚子隨機應變的鬼主意,更是那一手錶里不一、裝傻充愣、扮豬吃老虎的絕活。
「糊塗」,是他韋小寶行走江湖、安身立命的護身符。
可現在,他老了,油盡燈枯,躺在這把用金絲楠木打造的躺椅上,連站起來都費勁。死亡的氣息像院子裡石縫中的青苔,悄無聲息地,卻又無孔不入地蔓延到他身體的每一個角落。當一個人真正感覺到自己快要死了,他反而比任何時候都渴望一件事——「明白」。
他開始不受控制地回想過去,那些被他刻意用「糊塗」掩蓋掉的、不願深究的細節,像退潮後沙灘上兀然露出的尖利石子,密密麻麻,硌得他心裡一陣陣地生疼。
午後,為了給老太爺解悶,府里的幾個兒子和侄子輩的年輕人在後院寬闊的草場上จัด起了一場馬球賽。這是韋家多年來的傳統項目,男丁們從小就要學騎馬,幾個兒子更是此中好手。
韋小寶被眾人簇擁著,坐在觀賽台上最好的位置,身上蓋著厚厚的毯子。身邊坐著蘇荃、雙兒、建寧等幾位夫人。蘇荃依舊是那副當慣了教主夫人的派頭,端莊持重,不苟言笑,手裡捻著一串佛珠,目光平靜地看著場內。她掌管著韋家偌大的家業,是這後宅真正的「定海神針」。
場上的比賽正激烈。幾個兒子分成兩隊,縱馬馳騁,揮桿爭搶。馬蹄翻飛,草屑四濺,呼喝叫好之聲、球桿清脆的撞擊聲混成一片,好不熱鬧。
韋小寶的目光,卻不由自主地被場上的一道身影牢牢吸引住了。
那是阿珂的兒子,韋虎。
他今年剛二十出頭,是所有兒子裡相貌最為出眾的一個。他繼承了阿珂那天下無雙的美貌,又糅合了男子的英氣,劍眉星目,俊朗不凡。此刻他一身利落的騎裝,騎在一匹神駿非凡的通體雪白的馬上,身姿挺拔如松,馬術精湛得不像話。只見他一個漂亮的側身,宛如靈猿探臂,從對手的球桿下將木球穩穩截走,隨即長臂一揮,手腕發力,那顆木球便如一道白色的閃電,呼嘯著飛出,應聲滾入球門。
「好!」滿場爆發出雷鳴般的喝彩聲。
韋虎勒住韁繩,白馬人立而起,發出一聲長嘶。他穩穩地坐在馬背上,臉上露出一個得意的笑容。他沒有像韋小寶的其他兒子那樣興奮地大呼小叫,只是在馬背上微微側過身,衝著喝彩的眾人,極其輕微地、幾乎難以察覺地揚起了下巴。那眼神里,帶著一絲渾然天成的倨傲,一種仿佛與生俱來的、睥睨眾生的貴氣。
就是這個動作。
這個快到幾乎無法捕捉的微不足道的神態。
「哐當!」一聲脆響。
韋小寶手裡端著的那隻上好的龍泉窯青瓷茶杯,毫無徵兆地滑落在地,摔了個粉碎。滾燙的茶水濺濕了他的袍角和鞋面,他卻渾然不覺,仿佛被施了定身法。
「相公,怎麼了?可是哪裡不舒服?燙著沒有?」雙兒最先反應過來,連忙蹲下身,一邊用帕子給他擦拭,一邊關切地問。
韋小寶沒有回答。他的眼睛死死地盯著遠處的韋虎,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在那一瞬間凝固了,手腳冰涼。他見過那個神態,太熟悉了,熟悉到刻骨銘心。當年在台灣,那個處處與他作對,搶走了阿珂,讓他恨得牙痒痒的延平郡王三公子,那個被他用計坑害得身敗名裂、狼狽不堪的「小白臉」——鄭克塽,在他得志時,就是這個樣子!
一樣的俊俏臉龐,一樣的倨傲神氣,仿佛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一種血脈裡帶出來的,學都學不像的矜貴!
「老爺?老爺您怎麼了?」蘇荃也察覺到了他的不對勁,放下佛珠,皺眉問道,語氣裡帶著一絲擔憂。
韋小寶猛地回過神來,臉上瞬間又掛上了那副幾十年不變的、賴皮的笑容,只是這笑容顯得無比僵硬。「哎呀,老了老了,手不中用了,連個杯子都拿不穩。可惜了這上好的普洱,可惜了,可惜了!」
他一邊打著哈哈,一邊用眼角的餘光飛快地瞥向身旁的阿珂。阿珂還是那副冷冰冰的樣子,仿佛對場上的勝負和兒子的英姿都漠不關心,只是靜靜地看著遠處雲霧繚繞的雪山,好像那裡的風景比眼前的一切都更吸引她。她的臉上,看不出任何情緒。
韋小寶心裡猛地一沉。他拚命地在心裡安慰自己,是老眼昏花,想多了。天下長得像的人多了去了,或許只是巧合,年輕人嘛,少年得志,有點傲氣也正常。可是,那個畫面就像一根淬了毒的細針,狠狠地扎進了他的心臟,拔不出來,還隨著血脈的每一次搏動,把那冰冷的毒液帶到四肢百骸。他覺得手腳發麻,心口堵得像塞了一團濕棉花。
他這一輩子,最引以為傲的風流事,就是把天下第一美人阿珂搶到了手,哪怕用的是些見不得光的下三濫手段。他一直覺得,人是他的,生的兒子自然也就是他的。可今天,這個他篤信了幾十年的念頭,就像一塊長了霉斑的牆皮,被韋虎那個不經意的神態輕輕一戳,就「嘩啦」一下,掉下一大塊,露出了裡面潮濕、醜陋、不堪入目的底子。
他強迫自己移開目光,想看看別的兒子,尋求一些心理上的安慰。他的大兒子韋豹,雙兒所生,性子最像他,機靈圓滑,此刻正咋咋呼呼地在場邊指揮隊友,上躥下跳,滿臉都是他年輕時那股子活泛勁兒。看到韋豹,他心裡稍安。他又看向別的孩子,有的敦厚,有的文弱,各有各的模樣,多多少少都能從他和他們母親身上找到些影子。
他試圖讓自己相信,孩子嘛,長得像誰都有可能,像舅舅,像姥爺,隔代遺傳,都是說得通的。
就在他這麼翻來覆去地勸說自己的時候,場上起了小小的衝突。
比賽結束了,韋虎那隊理所當然地贏了。輸了的一方,建寧公主的兒子韋冬,臉上有些掛不住,悶悶不樂地牽著馬往回走。一個同隊的表親也是個沒眼力見的,湊過來拍了拍他的肩膀,半開玩笑地說道:「冬少爺,今天可是被虎少爺搶盡了風頭啊,咱們技不如人,甘拜下風,哈哈。」
這句話本是一句緩和氣氛的無心之言,韋冬卻猛地停下腳步,臉色一沉。
他沒有像他那個瘋瘋癲癲的娘建寧公主那樣跳起來罵人,也不是像他爹韋小寶那樣嘻嘻哈哈地插科打諢糊弄過去。他只是停了下來,轉過身,負手而立。他臉上的表情很淡,甚至沒有看那個說話的表親,目光平靜地投向遠方碧藍的天空,用一種與他二十歲年紀完全不符的沉穩語調,一字一句地說道:「一場遊戲罷了,勝負乃常事。此事到此為止,休得再提。」
他的聲音不高,不疾不徐,卻帶著一種令人無法抗拒的、天生的威嚴。那個表親被他這股不怒自威的氣勢鎮住了,臉上的笑容頓時僵住,訕訕地閉上了嘴,大氣都不敢再出半聲。
這一下,比剛才韋虎那個倨傲的神情,更讓韋小寶如遭雷擊。
他整個人都僵在了躺椅上,瞳孔在一瞬間收縮。他猛地想起了一個人,一個他既敬畏又熟悉,甚至曾經同床共枕過的人——年輕時的康熙皇帝,他的「小玄子」。
當年在紫禁城的御書房裡,小玄子決定要除掉權傾朝野的鰲拜時,就是用這種口氣跟自己說話的。平時可以沒大沒小地打打鬧鬧,一旦涉及國事,那份生殺予奪的帝王之氣就自然而然地從骨子裡流露出來,讓人心頭髮顫,不敢有半分違逆。
韋冬的這個樣子,這股子發號施令的勁兒,簡直和小玄子年少時一模一樣!分毫不差!
一個無比可怕的、他從來不敢去想的念頭,像一條蟄伏已久的毒蛇,猛地從他心底最黑暗的角落竄了出來,吐著信子,亮出了致命的毒牙:建寧那婆娘,刁蠻任性,當年歸隱之前,最是思念京城繁華,借著省親的名義回過好幾次宮……有一次,還在宮裡住了小半年才磨磨蹭蹭地回來……
「轟」的一聲,韋小寶覺得天旋地轉,眼前發黑,耳邊嗡嗡作響。他頓時覺得手腳冰涼,連指甲縫裡都是冷的。麗江午後那般暖洋洋的太陽,此刻照在他身上,卻再也驅不散那股從心底、從靈魂深處冒出來的徹骨寒意。
如果說,對韋虎的懷疑還只是一根細細的針,偶爾刺痛一下。那麼,對韋冬的這個念頭,簡直就是一把千斤重的攻城巨錘,狠狠地砸在了他心門上,把他心裡那點僅存的僥倖和自欺欺人,砸了個稀巴爛。
他覺得自己像個傻子,一個天底下最大的傻子。忙活了一輩子,到頭來,不光可能幫情敵養兒子,還可能幫皇帝養兒子。這傳出去,他韋小寶的臉還往哪兒擱?
02
那一天剩下的時間,韋小寶是怎麼過的,他自己都記不清了。
他只知道,夫人們後來的說笑,孫子們的打鬧,下人們謙卑的奉承,都像隔著一層厚厚的水幕,嗡嗡作響,模糊不清,卻一個字也進不了他的耳朵。
他的腦子裡,反反覆復、來來回回,就是兩個揮之不去的畫面:一個是韋虎在馬背上揚起下巴的倨傲,另一個是韋冬負手而立的沉穩。
這兩個畫面,像兩隻無形的手,死死地掐住了他的喉嚨,讓他喘不過氣來。又像兩塊燒紅的烙鐵,交替著在他心上烙印,讓他痛不欲生。
晚宴上,闔家團圓,一派熱鬧。韋小寶破天荒地沒怎麼說話,也沒了平日裡講兩個從麗春院聽來的葷段子逗大家笑的興致。
他就那麼枯坐著,一雙眼睛空洞地望著桌上的菜肴,面前的酒杯空了,就自己滿上,然後一飲而盡,辛辣的酒液順著喉管一直燒到胃裡。
雙兒看在眼裡,疼在心裡,悄悄拉了拉他的袖子,柔聲勸他:「相公,少喝點吧,大夫說酒最傷身子,您這幾日咳得厲害。」
韋小寶抬起渾濁的眼睛看了她一眼,咧嘴一笑,那笑容比哭還難看:「沒事兒,老子這輩子,什麼沒嘗過?人參鹿茸,鶴頂紅砒霜,都吃過。就這點馬尿,還放不倒我。」
他說的是「老子」,而不是往常在雙兒面前自稱的「我」。只有在他心裡極度煩躁或者憤怒的時候,他才會用這個在揚州市井裡混跡時養成的粗魯自稱。蘇荃和雙兒對視一眼,都從對方眼中看到了濃濃的憂慮,但她們都默契地沒有再說什麼,只是默默地往他碗里夾菜。
夜深人靜,妻妾們各自回房。韋小寶以身體不適為由,獨自歇在了自己的主屋。他躺在寬大的床上,睜著眼睛,毫無睡意。白天的兩個畫面在他腦中不斷盤旋,攪得他心煩意亂,五臟六腑都像錯了位。他索性閉上眼,任由思緒的野馬掙脫韁繩,開始瘋狂地回憶過去。
他想起了阿珂。
他想起了第一次在河南少林寺外的山道上見到她。她一身素衣,卻美得讓他心跳都漏了一拍,他當時就暗暗發誓,這個女人,他韋小寶要定了,不管用什麼法子。
他想起了在平西王府,他為了她,不惜得罪吳三桂的寶貝兒子吳應熊。想起了在台灣,他耍盡了陰謀詭計,利用天地會的勢力,離間她和鄭克塽,把那個在他看來除了長得俊一無是處的「小白臉」的名聲徹底搞臭。
最後,是揚州。那個煙花叢中的麗春院,他自己的「老家」。在那個昏暗的房間裡,他用最卑劣的、他自己都有些不齒的手段,在酒里下了迷藥,占有了她,也占有了同樣被迷暈的蘇荃。
他一直認為,這是他一生中辦得最「漂亮」、最得意的一件事。
大丈夫敢愛敢恨,看上了就要搶過來,天經地義。他一直以為,生米煮成了熟飯,人心自然也就慢慢收回來了。孩子生下來,當了娘,就像拴上了鏈子的鷹,還能撲騰著翅膀飛到哪兒去?
現在想來,他錯了。大錯特錯。
這麼多年,阿珂對他,何曾有過半分溫情?除了在床笫之間必要的、像是完成任務一樣的迎合,她看他的眼神,永遠是冷的,疏離的,像是在看一個不相干的陌生人。他們之間,隔著一片看不見的海,他永遠也渡不過去。他們更像是主人與囚犯,而不是丈夫與妻子。她在這個喧囂熱鬧的大家庭里,活得像個最熟悉的陌生人,清冷又孤僻。
那顆被鄭克塽偷走的心,他韋小寶用盡了權勢、金錢和手段,花了二十多年的光陰,也沒能給搶回來。
他越想越氣,越想越覺得恥辱。他韋小寶是什麼人?皇帝跟前平起平坐的大紅人,天地會的總舵主(雖然是假的),走到哪兒不是前呼後擁,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怎麼到了一個女人身上,就栽了這麼大的一個跟頭?還可能……還可能傻乎乎地替別人養了二十年的兒子!這簡直是奇恥大辱!
「不行,我得去問問她!我非得問個明白!」一個念頭在他心裡扎了根,瘋了一樣地生長。
第二天,韋小寶起了個大早。他沒讓雙兒扶,自己撐著一根沉香木的拐杖,步履蹣跚,一步一步地挪到了阿珂居住的那個清幽的小院。
阿珂的院子是整個韋府最清靜的地方。她不喜奢華,院裡只種了些素雅的蘭花和幾竿瘦長的翠竹,地上鋪著青石板,打掃得一塵不染。
此刻,她正穿著一身月白色的素服,坐在窗前,手裡拿著一卷佛經,神態安詳,仿佛已是方外之人。
韋小寶走進去的時候,故意用拐杖「篤篤篤」地敲擊著地面,弄出些聲響。阿珂抬起頭,看到是他,那雙總是淡漠如水的眼眸里,飛快地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波瀾,隨即又恢復了古井無波的平靜。
她站起身,隔著幾步遠的距離,淡淡地行了一禮:「老爺怎麼過來了?」
這一聲「老爺」,叫得客氣,卻也像一把尺子,把兩人的距離量得清清楚楚,無比遙遠。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本文所用素材源於網際網路,部分圖片非真實圖像,僅用於敘事呈現,請知悉
在雲南麗江的暖陽下,曾經攪動天下風雲的鹿鼎公韋小寶,已是行將就木的古稀老人。
他坐擁著潑天富貴,享受著七位夫人和滿堂兒孫的環繞,這份看似圓滿的天倫之樂,本應是他傳奇一生最安詳的句點。
這份平靜之下,懷疑的陰影卻早已如毒藤般悄然滋生,纏繞住他日漸衰竭的心脈。
他審視著一張張熟悉又陌生的子孫面孔,那些不經意間流露出的、與自己迥異的神態和氣度,像一根根尖刺,扎在他裝糊塗了大半生的面具上,讓他覺得自己像一個天大的笑話。
當生命的燈火即將燃盡,他用盡最後一口氣,將七位夫人悉數叫到床前。
在昏暗的燭光與女人們複雜的目光中,這個一生都在嬉笑怒罵中求生的男人,攥緊了她們的手,問出了那個足以摧毀一切的、顫抖著的問題……
01
雲南,麗江。
這座遠離了京城喧囂的古城,用它特有的慵懶和溫吞,將一個曾經攪動了大清王朝風雲的男人,打磨成了一個安詳富足的古稀老人。
韋家的府邸,是整個麗江城裡最氣派的所在。三進三出的大院子,亭台樓閣,雕樑畫棟,後院引了玉龍雪山的活水,繞著假山潺潺流淌,養著從江南運來的名貴錦鯉。
府里的下人,從管家到燒火的丫頭,都知道韋老爺富可敵國,當年是隨著聖駕平定吳三桂的大功臣,封過一等鹿鼎公,連當今皇上,都得尊稱他一聲「桂貝勒」,私下裡或許還會親昵地叫一聲「小桂子」。
可這些輝煌,都已經是陳芝麻爛穀子的舊事了。如今的韋小寶,更像個尋常的富家翁,一個被歲月和舊傷徹底掏空了精氣神的老頭兒。他的背駝了,頭髮白得像玉龍山的雪,臉上布滿了老年斑,走幾步路就要喘上半天。
清晨的陽光透過精緻的雕花窗欞,斑駁地灑在紫檀木的拔步大床上。韋小寶在一陣撕心裂肺的咳嗽聲中醒來,咳得整個人都蜷縮成了蝦米,感覺肺葉子都要從喉嚨里翻出來了。守在床邊的雙兒立刻端上溫熱的蜜水,用那雙幾十年如一日溫柔的手,輕輕拍著他的後背。
「相公,慢點兒,順順氣。」她的聲音還是那麼軟糯,像是能撫平世間一切的焦躁。
韋小寶喝了水,喉嚨里那股子鐵鏽般的腥甜感才稍稍壓下去一些。他靠在幾個厚實的雲錦枕頭上,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一雙曾經精光四射的眼睛如今變得渾濁不堪,望著窗外。院子裡的三角梅開得潑辣又張揚,像一團燒得正旺的火。可他只覺得身上發冷,那股子從骨頭縫裡絲絲縷縷透出來的寒意,是再厚的狐皮被子也捂不熱的。
「雙兒,扶我出去走走。」他的聲音沙啞得厲害。
「哎,」雙兒應著,手腳麻利地取來一件織錦鑲白狐毛的披風給他仔細穿上,「大夫囑咐了,您這老寒腿最怕見風。咱們就在廊下坐坐,曬曬太陽,暖和暖和身子,好不好?」
韋小寶沒力氣爭辯,哼唧了一聲,算是默許了。
雙兒的力氣比年輕時小多了,但依舊是他最穩固的依靠。她幾乎是半抱著,才將他那副乾癟的身體挪到了院中廊下的紫藤蘿躺椅上。陽光照在臉上,暖洋洋的,他舒服地眯起了眼睛。幾個年紀小點的孫子孫女像一群小麻雀,嘰嘰喳喳地跑過來,圍著他「爺爺、爺爺」地叫個不停,把剝好的橘子瓣兒往他嘴裡塞。
韋小寶臉上擠出一絲皺巴巴的笑容,從懷裡摸出幾塊早就準備好的麥芽糖,顫巍巍地遞給他們。「吃吧,吃吧,都是好孩子,都長高了……」
他看著這滿院的兒孫,大的已經娶妻生子,在外面獨當一面;小的還在咿呀學語,繞著他的腿打轉。一張張鮮活的面孔,本該是他韋小寶這一生最得意、最值得吹噓的成就。可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看他們的眼神變了。那種發自內心的、天倫之樂的欣慰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近乎審視的、帶著探究的陌生目光。
他這一輩子,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紫禁城裡跟小玄子摔跤打鬧,天地會裡當香主指點江山,神龍島上做白龍使虛與委蛇。他靠的是什麼?不是那一身不入流的武功,更不是那斗大的字認不了一籮筐的學問。
他靠的,是他那顆比誰都轉得快的腦子,是那一肚子隨機應變的鬼主意,更是那一手錶里不一、裝傻充愣、扮豬吃老虎的絕活。
「糊塗」,是他韋小寶行走江湖、安身立命的護身符。
可現在,他老了,油盡燈枯,躺在這把用金絲楠木打造的躺椅上,連站起來都費勁。死亡的氣息像院子裡石縫中的青苔,悄無聲息地,卻又無孔不入地蔓延到他身體的每一個角落。當一個人真正感覺到自己快要死了,他反而比任何時候都渴望一件事——「明白」。
他開始不受控制地回想過去,那些被他刻意用「糊塗」掩蓋掉的、不願深究的細節,像退潮後沙灘上兀然露出的尖利石子,密密麻麻,硌得他心裡一陣陣地生疼。
午後,為了給老太爺解悶,府里的幾個兒子和侄子輩的年輕人在後院寬闊的草場上จัด起了一場馬球賽。這是韋家多年來的傳統項目,男丁們從小就要學騎馬,幾個兒子更是此中好手。
韋小寶被眾人簇擁著,坐在觀賽台上最好的位置,身上蓋著厚厚的毯子。身邊坐著蘇荃、雙兒、建寧等幾位夫人。蘇荃依舊是那副當慣了教主夫人的派頭,端莊持重,不苟言笑,手裡捻著一串佛珠,目光平靜地看著場內。她掌管著韋家偌大的家業,是這後宅真正的「定海神針」。
場上的比賽正激烈。幾個兒子分成兩隊,縱馬馳騁,揮桿爭搶。馬蹄翻飛,草屑四濺,呼喝叫好之聲、球桿清脆的撞擊聲混成一片,好不熱鬧。
韋小寶的目光,卻不由自主地被場上的一道身影牢牢吸引住了。
那是阿珂的兒子,韋虎。
他今年剛二十出頭,是所有兒子裡相貌最為出眾的一個。他繼承了阿珂那天下無雙的美貌,又糅合了男子的英氣,劍眉星目,俊朗不凡。此刻他一身利落的騎裝,騎在一匹神駿非凡的通體雪白的馬上,身姿挺拔如松,馬術精湛得不像話。只見他一個漂亮的側身,宛如靈猿探臂,從對手的球桿下將木球穩穩截走,隨即長臂一揮,手腕發力,那顆木球便如一道白色的閃電,呼嘯著飛出,應聲滾入球門。
「好!」滿場爆發出雷鳴般的喝彩聲。
韋虎勒住韁繩,白馬人立而起,發出一聲長嘶。他穩穩地坐在馬背上,臉上露出一個得意的笑容。他沒有像韋小寶的其他兒子那樣興奮地大呼小叫,只是在馬背上微微側過身,衝著喝彩的眾人,極其輕微地、幾乎難以察覺地揚起了下巴。那眼神里,帶著一絲渾然天成的倨傲,一種仿佛與生俱來的、睥睨眾生的貴氣。
就是這個動作。
這個快到幾乎無法捕捉的微不足道的神態。
「哐當!」一聲脆響。
韋小寶手裡端著的那隻上好的龍泉窯青瓷茶杯,毫無徵兆地滑落在地,摔了個粉碎。滾燙的茶水濺濕了他的袍角和鞋面,他卻渾然不覺,仿佛被施了定身法。
「相公,怎麼了?可是哪裡不舒服?燙著沒有?」雙兒最先反應過來,連忙蹲下身,一邊用帕子給他擦拭,一邊關切地問。
韋小寶沒有回答。他的眼睛死死地盯著遠處的韋虎,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在那一瞬間凝固了,手腳冰涼。他見過那個神態,太熟悉了,熟悉到刻骨銘心。當年在台灣,那個處處與他作對,搶走了阿珂,讓他恨得牙痒痒的延平郡王三公子,那個被他用計坑害得身敗名裂、狼狽不堪的「小白臉」——鄭克塽,在他得志時,就是這個樣子!
一樣的俊俏臉龐,一樣的倨傲神氣,仿佛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一種血脈裡帶出來的,學都學不像的矜貴!
「老爺?老爺您怎麼了?」蘇荃也察覺到了他的不對勁,放下佛珠,皺眉問道,語氣裡帶著一絲擔憂。
韋小寶猛地回過神來,臉上瞬間又掛上了那副幾十年不變的、賴皮的笑容,只是這笑容顯得無比僵硬。「哎呀,老了老了,手不中用了,連個杯子都拿不穩。可惜了這上好的普洱,可惜了,可惜了!」
他一邊打著哈哈,一邊用眼角的餘光飛快地瞥向身旁的阿珂。阿珂還是那副冷冰冰的樣子,仿佛對場上的勝負和兒子的英姿都漠不關心,只是靜靜地看著遠處雲霧繚繞的雪山,好像那裡的風景比眼前的一切都更吸引她。她的臉上,看不出任何情緒。
韋小寶心裡猛地一沉。他拚命地在心裡安慰自己,是老眼昏花,想多了。天下長得像的人多了去了,或許只是巧合,年輕人嘛,少年得志,有點傲氣也正常。可是,那個畫面就像一根淬了毒的細針,狠狠地扎進了他的心臟,拔不出來,還隨著血脈的每一次搏動,把那冰冷的毒液帶到四肢百骸。他覺得手腳發麻,心口堵得像塞了一團濕棉花。
他這一輩子,最引以為傲的風流事,就是把天下第一美人阿珂搶到了手,哪怕用的是些見不得光的下三濫手段。他一直覺得,人是他的,生的兒子自然也就是他的。可今天,這個他篤信了幾十年的念頭,就像一塊長了霉斑的牆皮,被韋虎那個不經意的神態輕輕一戳,就「嘩啦」一下,掉下一大塊,露出了裡面潮濕、醜陋、不堪入目的底子。
他強迫自己移開目光,想看看別的兒子,尋求一些心理上的安慰。他的大兒子韋豹,雙兒所生,性子最像他,機靈圓滑,此刻正咋咋呼呼地在場邊指揮隊友,上躥下跳,滿臉都是他年輕時那股子活泛勁兒。看到韋豹,他心裡稍安。他又看向別的孩子,有的敦厚,有的文弱,各有各的模樣,多多少少都能從他和他們母親身上找到些影子。
他試圖讓自己相信,孩子嘛,長得像誰都有可能,像舅舅,像姥爺,隔代遺傳,都是說得通的。
就在他這麼翻來覆去地勸說自己的時候,場上起了小小的衝突。
比賽結束了,韋虎那隊理所當然地贏了。輸了的一方,建寧公主的兒子韋冬,臉上有些掛不住,悶悶不樂地牽著馬往回走。一個同隊的表親也是個沒眼力見的,湊過來拍了拍他的肩膀,半開玩笑地說道:「冬少爺,今天可是被虎少爺搶盡了風頭啊,咱們技不如人,甘拜下風,哈哈。」
這句話本是一句緩和氣氛的無心之言,韋冬卻猛地停下腳步,臉色一沉。
他沒有像他那個瘋瘋癲癲的娘建寧公主那樣跳起來罵人,也不是像他爹韋小寶那樣嘻嘻哈哈地插科打諢糊弄過去。他只是停了下來,轉過身,負手而立。他臉上的表情很淡,甚至沒有看那個說話的表親,目光平靜地投向遠方碧藍的天空,用一種與他二十歲年紀完全不符的沉穩語調,一字一句地說道:「一場遊戲罷了,勝負乃常事。此事到此為止,休得再提。」
他的聲音不高,不疾不徐,卻帶著一種令人無法抗拒的、天生的威嚴。那個表親被他這股不怒自威的氣勢鎮住了,臉上的笑容頓時僵住,訕訕地閉上了嘴,大氣都不敢再出半聲。
這一下,比剛才韋虎那個倨傲的神情,更讓韋小寶如遭雷擊。
他整個人都僵在了躺椅上,瞳孔在一瞬間收縮。他猛地想起了一個人,一個他既敬畏又熟悉,甚至曾經同床共枕過的人——年輕時的康熙皇帝,他的「小玄子」。
當年在紫禁城的御書房裡,小玄子決定要除掉權傾朝野的鰲拜時,就是用這種口氣跟自己說話的。平時可以沒大沒小地打打鬧鬧,一旦涉及國事,那份生殺予奪的帝王之氣就自然而然地從骨子裡流露出來,讓人心頭髮顫,不敢有半分違逆。
韋冬的這個樣子,這股子發號施令的勁兒,簡直和小玄子年少時一模一樣!分毫不差!
一個無比可怕的、他從來不敢去想的念頭,像一條蟄伏已久的毒蛇,猛地從他心底最黑暗的角落竄了出來,吐著信子,亮出了致命的毒牙:建寧那婆娘,刁蠻任性,當年歸隱之前,最是思念京城繁華,借著省親的名義回過好幾次宮……有一次,還在宮裡住了小半年才磨磨蹭蹭地回來……
「轟」的一聲,韋小寶覺得天旋地轉,眼前發黑,耳邊嗡嗡作響。他頓時覺得手腳冰涼,連指甲縫裡都是冷的。麗江午後那般暖洋洋的太陽,此刻照在他身上,卻再也驅不散那股從心底、從靈魂深處冒出來的徹骨寒意。
如果說,對韋虎的懷疑還只是一根細細的針,偶爾刺痛一下。那麼,對韋冬的這個念頭,簡直就是一把千斤重的攻城巨錘,狠狠地砸在了他心門上,把他心裡那點僅存的僥倖和自欺欺人,砸了個稀巴爛。
他覺得自己像個傻子,一個天底下最大的傻子。忙活了一輩子,到頭來,不光可能幫情敵養兒子,還可能幫皇帝養兒子。這傳出去,他韋小寶的臉還往哪兒擱?
02
那一天剩下的時間,韋小寶是怎麼過的,他自己都記不清了。
他只知道,夫人們後來的說笑,孫子們的打鬧,下人們謙卑的奉承,都像隔著一層厚厚的水幕,嗡嗡作響,模糊不清,卻一個字也進不了他的耳朵。
他的腦子裡,反反覆復、來來回回,就是兩個揮之不去的畫面:一個是韋虎在馬背上揚起下巴的倨傲,另一個是韋冬負手而立的沉穩。
這兩個畫面,像兩隻無形的手,死死地掐住了他的喉嚨,讓他喘不過氣來。又像兩塊燒紅的烙鐵,交替著在他心上烙印,讓他痛不欲生。
晚宴上,闔家團圓,一派熱鬧。韋小寶破天荒地沒怎麼說話,也沒了平日裡講兩個從麗春院聽來的葷段子逗大家笑的興致。
他就那麼枯坐著,一雙眼睛空洞地望著桌上的菜肴,面前的酒杯空了,就自己滿上,然後一飲而盡,辛辣的酒液順著喉管一直燒到胃裡。
雙兒看在眼裡,疼在心裡,悄悄拉了拉他的袖子,柔聲勸他:「相公,少喝點吧,大夫說酒最傷身子,您這幾日咳得厲害。」
韋小寶抬起渾濁的眼睛看了她一眼,咧嘴一笑,那笑容比哭還難看:「沒事兒,老子這輩子,什麼沒嘗過?人參鹿茸,鶴頂紅砒霜,都吃過。就這點馬尿,還放不倒我。」
他說的是「老子」,而不是往常在雙兒面前自稱的「我」。只有在他心裡極度煩躁或者憤怒的時候,他才會用這個在揚州市井裡混跡時養成的粗魯自稱。蘇荃和雙兒對視一眼,都從對方眼中看到了濃濃的憂慮,但她們都默契地沒有再說什麼,只是默默地往他碗里夾菜。
夜深人靜,妻妾們各自回房。韋小寶以身體不適為由,獨自歇在了自己的主屋。他躺在寬大的床上,睜著眼睛,毫無睡意。白天的兩個畫面在他腦中不斷盤旋,攪得他心煩意亂,五臟六腑都像錯了位。他索性閉上眼,任由思緒的野馬掙脫韁繩,開始瘋狂地回憶過去。
他想起了阿珂。
他想起了第一次在河南少林寺外的山道上見到她。她一身素衣,卻美得讓他心跳都漏了一拍,他當時就暗暗發誓,這個女人,他韋小寶要定了,不管用什麼法子。
他想起了在平西王府,他為了她,不惜得罪吳三桂的寶貝兒子吳應熊。想起了在台灣,他耍盡了陰謀詭計,利用天地會的勢力,離間她和鄭克塽,把那個在他看來除了長得俊一無是處的「小白臉」的名聲徹底搞臭。
最後,是揚州。那個煙花叢中的麗春院,他自己的「老家」。在那個昏暗的房間裡,他用最卑劣的、他自己都有些不齒的手段,在酒里下了迷藥,占有了她,也占有了同樣被迷暈的蘇荃。
他一直認為,這是他一生中辦得最「漂亮」、最得意的一件事。
大丈夫敢愛敢恨,看上了就要搶過來,天經地義。他一直以為,生米煮成了熟飯,人心自然也就慢慢收回來了。孩子生下來,當了娘,就像拴上了鏈子的鷹,還能撲騰著翅膀飛到哪兒去?
現在想來,他錯了。大錯特錯。
這麼多年,阿珂對他,何曾有過半分溫情?除了在床笫之間必要的、像是完成任務一樣的迎合,她看他的眼神,永遠是冷的,疏離的,像是在看一個不相干的陌生人。他們之間,隔著一片看不見的海,他永遠也渡不過去。他們更像是主人與囚犯,而不是丈夫與妻子。她在這個喧囂熱鬧的大家庭里,活得像個最熟悉的陌生人,清冷又孤僻。
那顆被鄭克塽偷走的心,他韋小寶用盡了權勢、金錢和手段,花了二十多年的光陰,也沒能給搶回來。
他越想越氣,越想越覺得恥辱。他韋小寶是什麼人?皇帝跟前平起平坐的大紅人,天地會的總舵主(雖然是假的),走到哪兒不是前呼後擁,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怎麼到了一個女人身上,就栽了這麼大的一個跟頭?還可能……還可能傻乎乎地替別人養了二十年的兒子!這簡直是奇恥大辱!
「不行,我得去問問她!我非得問個明白!」一個念頭在他心裡扎了根,瘋了一樣地生長。
第二天,韋小寶起了個大早。他沒讓雙兒扶,自己撐著一根沉香木的拐杖,步履蹣跚,一步一步地挪到了阿珂居住的那個清幽的小院。
阿珂的院子是整個韋府最清靜的地方。她不喜奢華,院裡只種了些素雅的蘭花和幾竿瘦長的翠竹,地上鋪著青石板,打掃得一塵不染。
此刻,她正穿著一身月白色的素服,坐在窗前,手裡拿著一卷佛經,神態安詳,仿佛已是方外之人。
韋小寶走進去的時候,故意用拐杖「篤篤篤」地敲擊著地面,弄出些聲響。阿珂抬起頭,看到是他,那雙總是淡漠如水的眼眸里,飛快地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波瀾,隨即又恢復了古井無波的平靜。
她站起身,隔著幾步遠的距離,淡淡地行了一禮:「老爺怎麼過來了?」
這一聲「老爺」,叫得客氣,卻也像一把尺子,把兩人的距離量得清清楚楚,無比遙遠。
 呂純弘 • 133K次觀看
呂純弘 • 133K次觀看 呂純弘 • 12K次觀看
呂純弘 • 12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花峰婉 • 17K次觀看
花峰婉 • 17K次觀看 呂純弘 • 10K次觀看
呂純弘 • 10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9K次觀看
呂純弘 • 9K次觀看 奚芝厚 • 9K次觀看
奚芝厚 • 9K次觀看 呂純弘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滿素荷 • 4K次觀看
滿素荷 • 4K次觀看 喬峰傳 • 34K次觀看
喬峰傳 • 34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24K次觀看
呂純弘 • 2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9K次觀看
呂純弘 • 49K次觀看 幸山輪 • 22K次觀看
幸山輪 • 22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