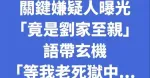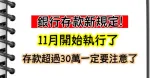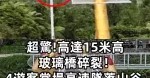3/3
下一頁
成功逃跑的鄔思道,為何沒救年羹堯?一場智與權的生死博弈

3/3
他做的是切割,是自保,更是放棄所有政治剩餘價值的歸零撤退。他知道,在絕對權力的秩序中,任何動念,都可能變成刃口。他不動,是最後的聰明。
他的逃,留住了命,也徹底斷了所有幻想。正因如此,他後來才能全身而退,成為雍正朝清洗運動中,極少數「脫離干係」的倖存者。
為何鄔思道不救年羹堯?
1726年,年羹堯被賜死。以九十二條大罪定案,帝王親下聖旨,明言「其罪深重,不可不斬」。他曾權傾朝野,最終卻連一句求情者都沒有,甚至連昔日的盟友都不見蹤影。
而鄔思道,正是最早離席之人。他沒有出現,沒有勸諫,也沒有託人上書。他從頭到尾,未言一語。人們問,既然曾有交情,為何不救?既然不是仇敵,為何不言?真相只有一個:年羹堯的命,早就不是一個人能救的了。
他不是死於哪條罪名,也不是敗在哪樁案情。他是死在結構里——在權力與制度的反噬中。他功高震主、驕橫跋扈,從封疆大吏走到獨斷專行。他讓巡撫跪迎,他不聽朝堂指令,他不再守臣子規矩。帝王已警覺,朝臣已反感,清洗只是遲早之事。
鄔思道早已看穿。他知道自己若出面,一是無效,二是自毀。他之所以沒救,是因為他懂得——帝心已決,乾綱獨斷,所有中間人、旁觀者、調解者,都會變成殉葬品。他不是棄舊盟,而是不願與之共沉。
更何況,年羹堯已不再是「可救之人」。他早已樹敵無數,從文臣到武將,從地方到中樞,無一不忌他權重。甚至在民間,也傳他驕奢淫逸、草菅人命。鄔思道作為讀書人,自有道義底線。他救的是朋友?還是一位既失節又失德的將軍?他自己心裡明白。
更殘酷的是,鄔思道不救,還因為他已看透官場的「連坐邏輯」:一旦救援失手,輕則被審,重則問斬。他不想成為第二個年羹堯。他不想多年籌謀,一朝盡毀。於是他逃,他斷,他沉默。不是冷酷,而是清醒。
這就是兩種命運的根本分野。年羹堯是行者,是攻者,是猛者。他敢立功,也敢犯忌。他走在前面,也死在前面。鄔思道是謀者,是避者,是守者。他不求名,不戀權,只求保全。一個攻出身亡,一個守得全生。
他們曾是並肩者,後來卻成了背影。一人載入帝王清單,刻上「叛逆」;一人留在民間軼聞,成為「智者」。這不是背叛,而是抉擇。不是冷血,而是定數。
最後,年羹堯死時,鄔思道仍在人間。只是他早已無聲。大廈將傾時,他早早走出門外,不為悲、不為喜,只為活。
他的逃,留住了命,也徹底斷了所有幻想。正因如此,他後來才能全身而退,成為雍正朝清洗運動中,極少數「脫離干係」的倖存者。
為何鄔思道不救年羹堯?
1726年,年羹堯被賜死。以九十二條大罪定案,帝王親下聖旨,明言「其罪深重,不可不斬」。他曾權傾朝野,最終卻連一句求情者都沒有,甚至連昔日的盟友都不見蹤影。
而鄔思道,正是最早離席之人。他沒有出現,沒有勸諫,也沒有託人上書。他從頭到尾,未言一語。人們問,既然曾有交情,為何不救?既然不是仇敵,為何不言?真相只有一個:年羹堯的命,早就不是一個人能救的了。
他不是死於哪條罪名,也不是敗在哪樁案情。他是死在結構里——在權力與制度的反噬中。他功高震主、驕橫跋扈,從封疆大吏走到獨斷專行。他讓巡撫跪迎,他不聽朝堂指令,他不再守臣子規矩。帝王已警覺,朝臣已反感,清洗只是遲早之事。
鄔思道早已看穿。他知道自己若出面,一是無效,二是自毀。他之所以沒救,是因為他懂得——帝心已決,乾綱獨斷,所有中間人、旁觀者、調解者,都會變成殉葬品。他不是棄舊盟,而是不願與之共沉。
更何況,年羹堯已不再是「可救之人」。他早已樹敵無數,從文臣到武將,從地方到中樞,無一不忌他權重。甚至在民間,也傳他驕奢淫逸、草菅人命。鄔思道作為讀書人,自有道義底線。他救的是朋友?還是一位既失節又失德的將軍?他自己心裡明白。
更殘酷的是,鄔思道不救,還因為他已看透官場的「連坐邏輯」:一旦救援失手,輕則被審,重則問斬。他不想成為第二個年羹堯。他不想多年籌謀,一朝盡毀。於是他逃,他斷,他沉默。不是冷酷,而是清醒。
這就是兩種命運的根本分野。年羹堯是行者,是攻者,是猛者。他敢立功,也敢犯忌。他走在前面,也死在前面。鄔思道是謀者,是避者,是守者。他不求名,不戀權,只求保全。一個攻出身亡,一個守得全生。
他們曾是並肩者,後來卻成了背影。一人載入帝王清單,刻上「叛逆」;一人留在民間軼聞,成為「智者」。這不是背叛,而是抉擇。不是冷血,而是定數。
最後,年羹堯死時,鄔思道仍在人間。只是他早已無聲。大廈將傾時,他早早走出門外,不為悲、不為喜,只為活。
 呂純弘 • 42K次觀看
呂純弘 • 42K次觀看 呂純弘 •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43K次觀看
呂純弘 • 43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舒黛葉 • 7K次觀看
舒黛葉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35K次觀看
呂純弘 • 35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奚芝厚 • 6K次觀看
奚芝厚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舒黛葉 • 3K次觀看
舒黛葉 • 3K次觀看 喬峰傳 • 5K次觀看
喬峰傳 • 5K次觀看 舒黛葉 • 8K次觀看
舒黛葉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38K次觀看
呂純弘 • 38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22K次觀看
呂純弘 • 22K次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