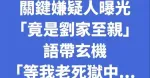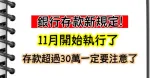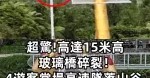1/3
下一頁
成功逃跑的鄔思道,為何沒救年羹堯?一場智與權的生死博弈

1/3
成功逃跑的鄔思道,為何沒救年羹堯?一場智與權的生死博弈
《——【·前言·】——》
1726年冬,年羹堯被賜死,那是雍正朝最震撼一幕。戰功赫赫的大將,瞬間跌入乞人慘境。
鄔思道——同樣扶持雍正上位的智囊,提前退隱,不僅安然無恙,還徹底消失在歷史主流。
相識與權力結構的隱秘
年羹堯在清朝雍正朝,曾是最耀眼的將領之一。他出身鑲白旗,個性果斷,行動利落。年輕時參加準噶爾戰役,一戰成名。1723年,雍正登基,挑選年羹堯為川陝總督,負責西北邊疆重任。正因生死同行、功業卓著,年羹堯成為雍正眼中不可多得的戰功支柱,可謂「帝國門戶守護者」。權重虎視,操兵百萬,號令如山動。與此同時,鄔思道這位出身書香門第的謀士,卻在朝堂上悄然嶄露頭角。
鄔思道出身並不顯赫,但見多識廣,擅長籌謀治學,尤其為雍正所賞識。他與年羹堯的相識,並非源自直接合作,而是源於一個微妙的身份牽連:年羹堯妹妹或堂妹年秋月,被安排在鄔思道身邊侍奉。這個安排表面是裙帶關係,實則是一種權力交換機制——年家通過親屬形式,嘗試拉攏智囊;朝廷也以此觀察年羹堯與謀士之間的連接脈絡。
年秋月這一人物雖然沒有明確出現在史書中,但在後世一些研究文章中被反覆提及。據說她被指派進入鄔思道為依傍之用,用以掌握政務信息與官員動態。這種做法,在那個時代並不罕見——權貴通過女性親屬安插在智囊身邊,既收視察之效,又具誘導牽制之用。鄔思道對此態度始終保持謹慎,他從未表現出過分親近,也從未利用家世背景上位。交情雖有,卻一直在謹慎保持距離之中。
在那個權力井然但暗潮湧動的時期,讓人無法忽視的是:年羹堯處于敏感位置,既掌握兵權,又承載邊疆穩定。雍正一方面信賴他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害怕他的權重對中央構成潛在威脅。鄔思道則處於風口浪尖,卻始終辦公謹慎。他深知,自己在朝堂,既不是線人,也不應成為某邊派系的散播者。他最擅長的,正是保持距離的藝術——不親不疏,不進不退。
二人關係起點如許,但後來卻漸行漸遠。年羹堯忙於戍邊、修堡、部署兵糧,從事軍事部署;鄔思道則留在京城,操持文案、議政、上書建議異常繁重。二人的路徑出現分歧,使命分庭而岔。細節描寫也很有感覺:有人說,在一次朝會後,年羹堯從御門下來,步履沉穩;鄔思道在幾步之外,整理公文,行色匆匆。彼此雖在同一個空間,卻如隔山。這樣的氣場差距,將成為後續命運分流的開端。
此時的朝局結構,也在定義兩人的前行軌跡。雍正帝實行嚴密考核制度,一旦軍功顯赫者稍有越界,就會被視為威脅而降格處理。官場上,無數高官抱怨雍正愛「得人心易,失人心難」,稍不留神,就可能成為政治犧牲品。年羹堯驍勇善戰,是雍正登基後治國距亂的重要支柱——可就是這種高度信任,也讓他處於「功高震主」的敏感位置。鄔思道正不同:他沒有兵卒沒有領軍的威名,只有文案、籌謀、建議。他的作用非直接衝鋒,而是幕後支撐。在朝中,他更像「太上參考」的角色,既出力又未顯山露水。
這種關係背景與結構定位,為後續對比提供了深刻張力。年羹堯憑戰功崛起、權重膨脹;鄔思道憑策劃隱退、保持低調。二者雖曾相識,卻在政治結構中默契分軌,最終走向兩個極端命運。章節的核心就是指出:二人「交集雖有」,卻不同命運;「權重雖近」,卻界限分明;「相關雖微」,卻決定生死轉折。
年羹堯的高光與墜落
年羹堯的輝煌起點是1723年。雍正帝登基伊始,即命年羹堯率兵進攻青海地區。年羹堯運籌帷幄,調配糧餉軍械,率部迅速征伐,結果斬獲叛將,震懾四方。朝中宣揚這一功績時,用詞簡練但鏗鏘有力:年羹堯「剿准載籍、定西北,坐擁鎮邊功臣封號」。他被賜封川陝總督,成為清朝邊疆鎮控重要角色,名聲迅速攀升。
他的軍事才能毋庸置疑,撫納回部分潤兵權等具體行動,甚至被紀錄在軍帳與史書中。雍正帝對此大加稱讚,批示:「君臣合力可立社稷」。年羹堯此後迅速獲得晉封,封號顯赫,茶馬制度、鹽政稅收、戍守戰略部署也在他掌控下運轉。他處理後勤、安撫民心、發放糧餉、擴充駐軍,其管理規模可匹敵重臣。
軍權的加持帶來的是人格與作風的急劇膨脹。年羹堯漸漸習慣於命令,他下令巡撫跪道侍迎,甚者命人修築馬道,不容其他官員通行。這類行為,被後世認定為「權傾一時、驕縱成性」。具體細節之一:他命令車隊經過某莊村,車轂必然頂撞路旁木樁,絕不允許村民以身體擋道;下屬官員若無提前報告,也被罰跪二十里。諸如此類細節,雖未寫進朝稿,卻在知府奏摺中頻頻出現,成為宮廷秘密之嫌。
年羹堯在發生這種權勢膨脹之際,對待反對者更加強硬。他撤換多位巡撫,迫令地方令史依其命令行事,甚至私設軍法,對偷竭、不服者處重刑。他的行為被朝堂視為越界。雍正帝對下屬曹可風等大臣暗示:「不可讓一個將領自命中心」,並以硃筆欽批:「功高不可驕,王法可施。」
1724年年羹堯第一次被革職調任南京,從川陝調離中央。這一時間節點很關鍵:那是他權勢開始被削弱的開端。調職先是「降移」,緊接著是降爵、抄家、取消軍事權柄。具體到文獻記載,年羹堯被要求交還所有軍權、交出印信,並停止參與朝政會議。他曾怒言不平,卻未能改變結局。他的下屬看到風聲變色,紛紛疏遠,幕客開始流失,仿佛在他的權力坍塌前夜,圍牆便開始翻裂。
1725年上半年,他再次被削權,貶至廬州、召還北京參與工營事,但無兵無權,權力徹底瓦解。與此同時,雍正帝下旨查年家帳冊,審查糧餉帳目,查漏補缺。審查中發現年羹堯侵犯地方稅收、營造軍營開支不明、與幕客瓜分軍餉等具體證據。這些成為他罪狀的重要組成。清算行動逐步推進,他的家屬財產被凍結,親屬被押回北京受調查。
這一路驟變,從將軍風範到階下囚死亡,只用了兩年不到。1725年底,朝廷正式定罪,逐項列出九十二條罪狀,包括「驕奢淫逸」「迫令巡撫督撫跪迎」「私調糧餉」等。調查中不僅牽扯年羹堯本人,還涉及其幕僚、私人屬僚,以及年羹堯在任期間涉及的租稅與軍事調動問題。係數之詳細,條款之嚴苛,反映了朝廷決心要將這位戰功將領徹底清算。
年羹堯之所以從極盛迅速墜入深淵,正因為他在雍正心目中已不是戰功的代言人,而成為帝王權力易位之後的潛在威脅。年羹堯的高光表現,與孜孜追求自身權力,將權勢膨脹到觸及皇權邊界。朝堂內外再無可容空間,雍正選擇以體制清算斷絕他的路線。年羹堯被革職、削爵、抄家、株連親屬,幾乎所有權力資源被一舉摘除。
《——【·前言·】——》
1726年冬,年羹堯被賜死,那是雍正朝最震撼一幕。戰功赫赫的大將,瞬間跌入乞人慘境。
鄔思道——同樣扶持雍正上位的智囊,提前退隱,不僅安然無恙,還徹底消失在歷史主流。
相識與權力結構的隱秘
年羹堯在清朝雍正朝,曾是最耀眼的將領之一。他出身鑲白旗,個性果斷,行動利落。年輕時參加準噶爾戰役,一戰成名。1723年,雍正登基,挑選年羹堯為川陝總督,負責西北邊疆重任。正因生死同行、功業卓著,年羹堯成為雍正眼中不可多得的戰功支柱,可謂「帝國門戶守護者」。權重虎視,操兵百萬,號令如山動。與此同時,鄔思道這位出身書香門第的謀士,卻在朝堂上悄然嶄露頭角。
鄔思道出身並不顯赫,但見多識廣,擅長籌謀治學,尤其為雍正所賞識。他與年羹堯的相識,並非源自直接合作,而是源於一個微妙的身份牽連:年羹堯妹妹或堂妹年秋月,被安排在鄔思道身邊侍奉。這個安排表面是裙帶關係,實則是一種權力交換機制——年家通過親屬形式,嘗試拉攏智囊;朝廷也以此觀察年羹堯與謀士之間的連接脈絡。
年秋月這一人物雖然沒有明確出現在史書中,但在後世一些研究文章中被反覆提及。據說她被指派進入鄔思道為依傍之用,用以掌握政務信息與官員動態。這種做法,在那個時代並不罕見——權貴通過女性親屬安插在智囊身邊,既收視察之效,又具誘導牽制之用。鄔思道對此態度始終保持謹慎,他從未表現出過分親近,也從未利用家世背景上位。交情雖有,卻一直在謹慎保持距離之中。
在那個權力井然但暗潮湧動的時期,讓人無法忽視的是:年羹堯處于敏感位置,既掌握兵權,又承載邊疆穩定。雍正一方面信賴他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害怕他的權重對中央構成潛在威脅。鄔思道則處於風口浪尖,卻始終辦公謹慎。他深知,自己在朝堂,既不是線人,也不應成為某邊派系的散播者。他最擅長的,正是保持距離的藝術——不親不疏,不進不退。
二人關係起點如許,但後來卻漸行漸遠。年羹堯忙於戍邊、修堡、部署兵糧,從事軍事部署;鄔思道則留在京城,操持文案、議政、上書建議異常繁重。二人的路徑出現分歧,使命分庭而岔。細節描寫也很有感覺:有人說,在一次朝會後,年羹堯從御門下來,步履沉穩;鄔思道在幾步之外,整理公文,行色匆匆。彼此雖在同一個空間,卻如隔山。這樣的氣場差距,將成為後續命運分流的開端。
此時的朝局結構,也在定義兩人的前行軌跡。雍正帝實行嚴密考核制度,一旦軍功顯赫者稍有越界,就會被視為威脅而降格處理。官場上,無數高官抱怨雍正愛「得人心易,失人心難」,稍不留神,就可能成為政治犧牲品。年羹堯驍勇善戰,是雍正登基後治國距亂的重要支柱——可就是這種高度信任,也讓他處於「功高震主」的敏感位置。鄔思道正不同:他沒有兵卒沒有領軍的威名,只有文案、籌謀、建議。他的作用非直接衝鋒,而是幕後支撐。在朝中,他更像「太上參考」的角色,既出力又未顯山露水。
這種關係背景與結構定位,為後續對比提供了深刻張力。年羹堯憑戰功崛起、權重膨脹;鄔思道憑策劃隱退、保持低調。二者雖曾相識,卻在政治結構中默契分軌,最終走向兩個極端命運。章節的核心就是指出:二人「交集雖有」,卻不同命運;「權重雖近」,卻界限分明;「相關雖微」,卻決定生死轉折。
年羹堯的高光與墜落
年羹堯的輝煌起點是1723年。雍正帝登基伊始,即命年羹堯率兵進攻青海地區。年羹堯運籌帷幄,調配糧餉軍械,率部迅速征伐,結果斬獲叛將,震懾四方。朝中宣揚這一功績時,用詞簡練但鏗鏘有力:年羹堯「剿准載籍、定西北,坐擁鎮邊功臣封號」。他被賜封川陝總督,成為清朝邊疆鎮控重要角色,名聲迅速攀升。
他的軍事才能毋庸置疑,撫納回部分潤兵權等具體行動,甚至被紀錄在軍帳與史書中。雍正帝對此大加稱讚,批示:「君臣合力可立社稷」。年羹堯此後迅速獲得晉封,封號顯赫,茶馬制度、鹽政稅收、戍守戰略部署也在他掌控下運轉。他處理後勤、安撫民心、發放糧餉、擴充駐軍,其管理規模可匹敵重臣。
軍權的加持帶來的是人格與作風的急劇膨脹。年羹堯漸漸習慣於命令,他下令巡撫跪道侍迎,甚者命人修築馬道,不容其他官員通行。這類行為,被後世認定為「權傾一時、驕縱成性」。具體細節之一:他命令車隊經過某莊村,車轂必然頂撞路旁木樁,絕不允許村民以身體擋道;下屬官員若無提前報告,也被罰跪二十里。諸如此類細節,雖未寫進朝稿,卻在知府奏摺中頻頻出現,成為宮廷秘密之嫌。
年羹堯在發生這種權勢膨脹之際,對待反對者更加強硬。他撤換多位巡撫,迫令地方令史依其命令行事,甚至私設軍法,對偷竭、不服者處重刑。他的行為被朝堂視為越界。雍正帝對下屬曹可風等大臣暗示:「不可讓一個將領自命中心」,並以硃筆欽批:「功高不可驕,王法可施。」
1724年年羹堯第一次被革職調任南京,從川陝調離中央。這一時間節點很關鍵:那是他權勢開始被削弱的開端。調職先是「降移」,緊接著是降爵、抄家、取消軍事權柄。具體到文獻記載,年羹堯被要求交還所有軍權、交出印信,並停止參與朝政會議。他曾怒言不平,卻未能改變結局。他的下屬看到風聲變色,紛紛疏遠,幕客開始流失,仿佛在他的權力坍塌前夜,圍牆便開始翻裂。
1725年上半年,他再次被削權,貶至廬州、召還北京參與工營事,但無兵無權,權力徹底瓦解。與此同時,雍正帝下旨查年家帳冊,審查糧餉帳目,查漏補缺。審查中發現年羹堯侵犯地方稅收、營造軍營開支不明、與幕客瓜分軍餉等具體證據。這些成為他罪狀的重要組成。清算行動逐步推進,他的家屬財產被凍結,親屬被押回北京受調查。
這一路驟變,從將軍風範到階下囚死亡,只用了兩年不到。1725年底,朝廷正式定罪,逐項列出九十二條罪狀,包括「驕奢淫逸」「迫令巡撫督撫跪迎」「私調糧餉」等。調查中不僅牽扯年羹堯本人,還涉及其幕僚、私人屬僚,以及年羹堯在任期間涉及的租稅與軍事調動問題。係數之詳細,條款之嚴苛,反映了朝廷決心要將這位戰功將領徹底清算。
年羹堯之所以從極盛迅速墜入深淵,正因為他在雍正心目中已不是戰功的代言人,而成為帝王權力易位之後的潛在威脅。年羹堯的高光表現,與孜孜追求自身權力,將權勢膨脹到觸及皇權邊界。朝堂內外再無可容空間,雍正選擇以體制清算斷絕他的路線。年羹堯被革職、削爵、抄家、株連親屬,幾乎所有權力資源被一舉摘除。
 呂純弘 • 42K次觀看
呂純弘 • 42K次觀看 呂純弘 •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43K次觀看
呂純弘 • 43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舒黛葉 • 7K次觀看
舒黛葉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35K次觀看
呂純弘 • 35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奚芝厚 • 6K次觀看
奚芝厚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舒黛葉 • 3K次觀看
舒黛葉 • 3K次觀看 喬峰傳 • 5K次觀看
喬峰傳 • 5K次觀看 舒黛葉 • 8K次觀看
舒黛葉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38K次觀看
呂純弘 • 38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22K次觀看
呂純弘 • 22K次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