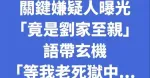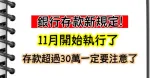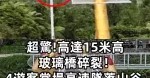3/4
下一頁
白崇禧婚內出軌產子,原配指著小三說:我不追究,但她要任我處置

3/4
在婚姻中,馬佩璋從未將自己定位成附庸,她是妻子,卻更像是將軍的左右手、家族的主心骨。
出軌風波
1930年代初,戰火尚未平息,桂系軍閥白崇禧風頭正盛,南征北討之間,一身戎裝殺伐果斷,背後又有一位剛烈聰慧的賢妻馬佩璋,簡直模範夫妻。
甚至有人在描繪這對夫妻時,用上了「琴瑟和鳴」「恩愛如山」的字眼,仿佛白崇禧是那個亂世中的一股清流。
可就在這樣一片清譽之下,風浪已然無聲地翻滾。
那年,戰局稍歇,白崇禧駐紮南寧。
他一個人坐在營帳中,對著地圖冥思苦想,副官許輝生看在眼裡,卻誤會了主帥的情緒。
他心想,長官身邊無女人,這般孤寂,恐怕早晚會出問題。
既然要安撫軍心,不如先安撫軍頭,便打起了「送美人」的主意。
第一次,他挑了幾個相貌出眾的女子,伺機獻上。
但白崇禧看了一眼,神情冷淡,揮手退人。
許輝生摸不准脈,心中暗忖,這位白狐狸不是不好女色,而是眼光太高,尋常脂粉根本入不了他的眼。
思來想去,忽然心頭一動,想到了自己在家鄉訂下的未婚妻,王氏。
王氏本是溫順柔婉的女子,雖出身平凡,卻端莊持重,原以為未婚夫忠厚可託付終身,哪知他竟會將她當成往上爬的踏腳石。
那天,許輝生帶著笑,語氣輕描淡寫地對她說:
「大帥身邊缺人照料,我要你前去服侍一段時間。」
王氏的臉色瞬間蒼白,她不敢相信這話是從自己未婚夫口中說出。
可她身在異鄉,無親無故,四處戰火又難歸家,再加上許輝生連番勸說,甚至動用情感綁架:
「你若真為我好,就聽我一次,成就我前程,也保你日後無憂。」
一番話說得王氏心如死灰,在淚眼中點了點頭,這一低頭,便是命運轉彎處。
王氏住進了白崇禧安排的新宅,她起初每日做飯、打掃、侍候飲茶,兩人相處半月,果然走到了一起。
許輝生如願以償,升了官,王氏成了「白將軍的女人」,白崇禧的眼中,終於有了「繼嗣」的可能。
後來,王氏懷孕了,生下了個男孩兒,白崇禧當然高興,這是他的第一個兒子。
他與馬佩璋育有兩個女兒,卻始終未得男嗣,這個男嬰的到來,讓他欣喜非常。
但這份喜悅,僅止於南寧宅邸的圍牆之內。
畢竟此事一旦傳出去,不僅有違他「模範丈夫」的形象,更可能引起政敵攻訐。
於是,他下令封鎖消息,將王氏與孩子安排在偏僻宅院,定期探望、送物資,卻從未帶入家族圈層。
可人心難封,風聲終究傳了出去。
遠在香港避難的馬佩璋,此時正一邊照料兩個年幼的女兒,一邊日日關注戰局消息,卻突然聽到了這樣一個傳聞,丈夫在南寧納妾生子,且是個男孩。
甚至有「好心人」言辭隱晦地提醒她:
「你得趕緊回去看看,聽說小的可是給他生了個大胖小子。」
馬佩璋或許從未想過白崇禧會背叛她,他們一起穿越戰火、共度生死,她為他守過病榻,為他打理家族,為他不懼戰火奔波,而他竟在她最不設防的時刻,給她捅了這一刀。
但這事,她必須要去解決。
沒有硝煙的對峙
馬佩璋抵達南寧的那天,裹著一身怒意和寒意。
消息傳到白崇禧耳中時,他正與幕僚議事。
聽說夫人到了南寧,面色瞬間僵住,竟無言以對。
他知道,馬佩璋不是那種會無的放矢的人,她既然來了,就意味著這件事已經鬧到「不可不收場」的地步了。
門剛打開,馬佩璋正倚窗而立,眼中沒有淚,也沒有火,只是極端的冷靜。
她沒有起身,也沒有看他,只是淡淡開口:「你來了。」
白崇禧張了張嘴,聲音在喉嚨里打轉:「你……聽說了?」
馬佩璋緩緩回頭,那眼神里沒有哭過的痕跡,反倒像個審問者:
「你覺得我不該聽說?」
他一時語塞,只能低頭,沉默,是最鋒利的刀。
良久,她開口,聲音清晰無比:
「白崇禧,我不是來哭的,也不是來鬧的,我是來處理事情的。」
她繼續道:「我只有兩個要求,其一,這事我不追究,但從今往後,她交給我處置,其二,孩子由我帶走。」
語氣平穩,沒有絲毫起伏,卻句句如釘,一錘一錘砸在人心上。
白崇禧下意識想說孩子是無辜的,王氏也不是無心之人。
但面對馬佩璋冷靜的目光,他終究沒有說出口,再多辯解,於她而言,不過是掩耳盜鈴。
馬佩璋這才緩了緩臉色,點了點頭:「我想親自與她談一談。」
第二天清晨,馬佩璋獨自前往王氏所居的小宅,王氏聞訊,已換了素衣,抱著孩子坐在床邊,神情惶然。
她原本以為馬佩璋會是怒氣衝天的模樣,最壞的打算是被打、被罵、被逐出南寧,可見到馬佩璋那一刻,她卻有些發愣,來人神色沉靜,不怒不躁。
馬佩璋看著眼前這位年輕女子,眼神沒有敵意,反而緩步走近,逕自坐下,說:「孩子給我抱抱。」
王氏下意識緊了緊懷裡的嬰兒,還是顫抖著把他遞了出去。
馬佩璋接過孩子,那動作熟練得讓王氏怔住,她抱孩子的手勢像極了一個母親,不,是更有經驗的母親。
孩子在她懷中竟慢慢止住了哭聲,安然入睡。
沉默中,王氏眼圈發紅,馬佩璋低頭看著孩子,語氣溫柔卻不容置疑:
「你是個聰明的姑娘,也知道這段關係,不屬於你,不怪你,但你不能留下。」
王氏咬著唇,眼淚終於滾了下來:「我……我捨不得他……」
「我懂。」馬佩璋抬起頭,看著她,「可你若真捨不得,就更該讓他有個名正言順的身份。在你身邊,他只是個私生子,在我這裡,他是白家的長子。」
王氏的眼神逐漸黯淡,她不是不懂,只是心不甘。
馬佩璋看穿她的猶豫,繼續說:
「我可以給你一筆錢,足夠你重新開始一段新生活,你還年輕,不該困死在這裡,你該好好過日子。」
她說這話的時候,語氣溫婉,像是在勸一位遠房的妹妹。
王氏的眼淚落得更厲害了,但她最終還是站起身,將孩子交還。
勝者無聲,敗者無恨。
這場對峙,沒有硝煙,卻勝似刀兵,是馬佩璋一生中最克制、也最智慧的戰鬥。
風波過後
馬佩璋抱著襁褓中的嬰兒,穿過白府的長廊,沒有人再提起王氏的名字,也沒有人敢對這名孩子的來歷多做揣測。
從這一刻起,這個孩子就是馬佩璋的兒子,是白家的長子,是「白先道」。
孩子抱回來之後,她一如對待其他兒女般喂養、呵護、教導,從不曾有絲毫差別。
有人雖知內情,卻誰也不敢質疑。
出軌風波
1930年代初,戰火尚未平息,桂系軍閥白崇禧風頭正盛,南征北討之間,一身戎裝殺伐果斷,背後又有一位剛烈聰慧的賢妻馬佩璋,簡直模範夫妻。
甚至有人在描繪這對夫妻時,用上了「琴瑟和鳴」「恩愛如山」的字眼,仿佛白崇禧是那個亂世中的一股清流。
可就在這樣一片清譽之下,風浪已然無聲地翻滾。
那年,戰局稍歇,白崇禧駐紮南寧。
他一個人坐在營帳中,對著地圖冥思苦想,副官許輝生看在眼裡,卻誤會了主帥的情緒。
他心想,長官身邊無女人,這般孤寂,恐怕早晚會出問題。
既然要安撫軍心,不如先安撫軍頭,便打起了「送美人」的主意。
第一次,他挑了幾個相貌出眾的女子,伺機獻上。
但白崇禧看了一眼,神情冷淡,揮手退人。
許輝生摸不准脈,心中暗忖,這位白狐狸不是不好女色,而是眼光太高,尋常脂粉根本入不了他的眼。
思來想去,忽然心頭一動,想到了自己在家鄉訂下的未婚妻,王氏。
王氏本是溫順柔婉的女子,雖出身平凡,卻端莊持重,原以為未婚夫忠厚可託付終身,哪知他竟會將她當成往上爬的踏腳石。
那天,許輝生帶著笑,語氣輕描淡寫地對她說:
「大帥身邊缺人照料,我要你前去服侍一段時間。」
王氏的臉色瞬間蒼白,她不敢相信這話是從自己未婚夫口中說出。
可她身在異鄉,無親無故,四處戰火又難歸家,再加上許輝生連番勸說,甚至動用情感綁架:
「你若真為我好,就聽我一次,成就我前程,也保你日後無憂。」
一番話說得王氏心如死灰,在淚眼中點了點頭,這一低頭,便是命運轉彎處。
王氏住進了白崇禧安排的新宅,她起初每日做飯、打掃、侍候飲茶,兩人相處半月,果然走到了一起。
許輝生如願以償,升了官,王氏成了「白將軍的女人」,白崇禧的眼中,終於有了「繼嗣」的可能。
後來,王氏懷孕了,生下了個男孩兒,白崇禧當然高興,這是他的第一個兒子。
他與馬佩璋育有兩個女兒,卻始終未得男嗣,這個男嬰的到來,讓他欣喜非常。
但這份喜悅,僅止於南寧宅邸的圍牆之內。
畢竟此事一旦傳出去,不僅有違他「模範丈夫」的形象,更可能引起政敵攻訐。
於是,他下令封鎖消息,將王氏與孩子安排在偏僻宅院,定期探望、送物資,卻從未帶入家族圈層。
可人心難封,風聲終究傳了出去。
遠在香港避難的馬佩璋,此時正一邊照料兩個年幼的女兒,一邊日日關注戰局消息,卻突然聽到了這樣一個傳聞,丈夫在南寧納妾生子,且是個男孩。
甚至有「好心人」言辭隱晦地提醒她:
「你得趕緊回去看看,聽說小的可是給他生了個大胖小子。」
馬佩璋或許從未想過白崇禧會背叛她,他們一起穿越戰火、共度生死,她為他守過病榻,為他打理家族,為他不懼戰火奔波,而他竟在她最不設防的時刻,給她捅了這一刀。
但這事,她必須要去解決。
沒有硝煙的對峙
馬佩璋抵達南寧的那天,裹著一身怒意和寒意。
消息傳到白崇禧耳中時,他正與幕僚議事。
聽說夫人到了南寧,面色瞬間僵住,竟無言以對。
他知道,馬佩璋不是那種會無的放矢的人,她既然來了,就意味著這件事已經鬧到「不可不收場」的地步了。
門剛打開,馬佩璋正倚窗而立,眼中沒有淚,也沒有火,只是極端的冷靜。
她沒有起身,也沒有看他,只是淡淡開口:「你來了。」
白崇禧張了張嘴,聲音在喉嚨里打轉:「你……聽說了?」
馬佩璋緩緩回頭,那眼神里沒有哭過的痕跡,反倒像個審問者:
「你覺得我不該聽說?」
他一時語塞,只能低頭,沉默,是最鋒利的刀。
良久,她開口,聲音清晰無比:
「白崇禧,我不是來哭的,也不是來鬧的,我是來處理事情的。」
她繼續道:「我只有兩個要求,其一,這事我不追究,但從今往後,她交給我處置,其二,孩子由我帶走。」
語氣平穩,沒有絲毫起伏,卻句句如釘,一錘一錘砸在人心上。
白崇禧下意識想說孩子是無辜的,王氏也不是無心之人。
但面對馬佩璋冷靜的目光,他終究沒有說出口,再多辯解,於她而言,不過是掩耳盜鈴。
馬佩璋這才緩了緩臉色,點了點頭:「我想親自與她談一談。」
第二天清晨,馬佩璋獨自前往王氏所居的小宅,王氏聞訊,已換了素衣,抱著孩子坐在床邊,神情惶然。
她原本以為馬佩璋會是怒氣衝天的模樣,最壞的打算是被打、被罵、被逐出南寧,可見到馬佩璋那一刻,她卻有些發愣,來人神色沉靜,不怒不躁。
馬佩璋看著眼前這位年輕女子,眼神沒有敵意,反而緩步走近,逕自坐下,說:「孩子給我抱抱。」
王氏下意識緊了緊懷裡的嬰兒,還是顫抖著把他遞了出去。
馬佩璋接過孩子,那動作熟練得讓王氏怔住,她抱孩子的手勢像極了一個母親,不,是更有經驗的母親。
孩子在她懷中竟慢慢止住了哭聲,安然入睡。
沉默中,王氏眼圈發紅,馬佩璋低頭看著孩子,語氣溫柔卻不容置疑:
「你是個聰明的姑娘,也知道這段關係,不屬於你,不怪你,但你不能留下。」
王氏咬著唇,眼淚終於滾了下來:「我……我捨不得他……」
「我懂。」馬佩璋抬起頭,看著她,「可你若真捨不得,就更該讓他有個名正言順的身份。在你身邊,他只是個私生子,在我這裡,他是白家的長子。」
王氏的眼神逐漸黯淡,她不是不懂,只是心不甘。
馬佩璋看穿她的猶豫,繼續說:
「我可以給你一筆錢,足夠你重新開始一段新生活,你還年輕,不該困死在這裡,你該好好過日子。」
她說這話的時候,語氣溫婉,像是在勸一位遠房的妹妹。
王氏的眼淚落得更厲害了,但她最終還是站起身,將孩子交還。
勝者無聲,敗者無恨。
這場對峙,沒有硝煙,卻勝似刀兵,是馬佩璋一生中最克制、也最智慧的戰鬥。
風波過後
馬佩璋抱著襁褓中的嬰兒,穿過白府的長廊,沒有人再提起王氏的名字,也沒有人敢對這名孩子的來歷多做揣測。
從這一刻起,這個孩子就是馬佩璋的兒子,是白家的長子,是「白先道」。
孩子抱回來之後,她一如對待其他兒女般喂養、呵護、教導,從不曾有絲毫差別。
有人雖知內情,卻誰也不敢質疑。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呂純弘 • 171K次觀看
呂純弘 • 171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41K次觀看
呂純弘 • 41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舒黛葉 • 4K次觀看
舒黛葉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28K次觀看
呂純弘 • 28K次觀看 呂純弘 • 10K次觀看
呂純弘 • 10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奚芝厚 • 5K次觀看
奚芝厚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17K次觀看
呂純弘 • 17K次觀看 舒黛葉 • 3K次觀看
舒黛葉 • 3K次觀看 喬峰傳 • 5K次觀看
喬峰傳 • 5K次觀看 舒黛葉 • 7K次觀看
舒黛葉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38K次觀看
呂純弘 • 38K次觀看 呂純弘 • 10K次觀看
呂純弘 • 10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10K次觀看
呂純弘 • 10K次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