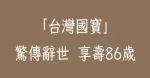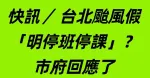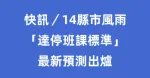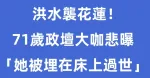3/3
下一頁
清軍無人能勸降洪承疇,20歲孝莊只身前往,說了什麼讓他剃髮易服

3/3
「皇兄!」多爾袞向前一步,聲音洪亮,「臣弟早就說過,跟這些漢人酸儒講道理是沒用的!他們最在乎的就是家人。派一隊兵,去福建南安,把他那個老娘和老婆孩子都抓到盛京來!就綁在院子外頭,一天不投降,就當著他的面抽一鞭子!臣弟不信,他洪承疇的心是鐵打的,能眼睜睜看著自己老娘替他受過!」
這個提議立刻在朝堂上引發了軒然大波。
「萬萬不可!」范文程第一個站出來,跪倒在地,幾乎是聲淚俱下,「皇上!此乃取死之道啊!洪承疇以忠孝立身,我們若以其母脅之,是逼他陷入忠孝不能兩全的絕境。到時候,他不但不會降,反而會立刻求死,以全孝道,免使其母受辱!此其一。其二,此舉一旦傳開,天下漢人會如何看我大清?會認為我大清乃是不顧人倫、行事卑劣的虎狼之邦!到那時,只會激起關內軍民更強烈的抵抗之心,天下所有有才之士,誰還敢歸附我大清?此舉是得一洪承疇之屍,而失盡天下之心啊!請皇上三思!」
「范大人此言差矣!」另一位滿洲將領反駁道,「婦人之仁!咱們打天下,靠的是刀把子,不是筆桿子!不給他們點顏色看看,他們永遠不知道誰才是主子!」
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在大殿內激烈地交鋒,一方主張鐵血手腕,一方主張攻心為上。皇太極坐在高高的龍椅上,聽著下面的爭吵,只覺得頭痛欲裂。他高大的身軀深深地陷在寶座里,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無力。
他既渴望得到洪承疇這把能打開中原大門的鑰匙,又深刻地明白范文程所說的政治後果。他不是一個只懂得殺戮的莽夫,他有著更宏大的政治抱負,他要的是整個天下,是人心所向。他的威嚴、他的智慧、他的寬宏,在洪承疇這塊沉默的頑石面前,仿佛統統失去了效用。
整個清廷上層,都被一種無計可施的陰雲所籠罩。
洪承疇的生死,已經超越了他個人,成了一個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的事件。
如果他就這麼餓死了,傳出去,就是他皇太極「德」不能感化明朝重臣,這對於一個意圖「以德服人」、取代大明正統的的政權來說,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污點和打擊。
這種集體性的挫敗感,達到了頂峰。它也為後續一個完全意想不到的人物的出場,營造了一個「非她不可」的絕望舞台。當所有的男人,無論是智者還是勇士,都宣告失敗之後,一個女人的登場,才更具石破天驚的戲劇性。
這天傍晚,軍醫送來了最後一次稟報。
「皇上……洪大人他……脈象微弱,氣息遊絲,瞳孔已經開始渙散……依微臣看,恐怕……恐怕撐不過今晚子時了。」
這個消息,如同一記重錘,徹底擊碎了皇太極心中最後一絲希望。他頹然地癱坐在龍椅上,沉默了許久,然後無力地揮了揮手,聲音里充滿了疲憊:「都退下吧……讓朕一個人靜一靜。」
大臣們躬身告退,沉重的腳步聲在空曠的大殿里漸行漸遠。很快,整個大殿里只剩下皇太極一個人。
窗外,天色已經完全暗了下來,殿內的燭火被穿堂風吹得搖曳不定,將他巨大的身影投射在冰冷的金磚上,拉得很長,很孤獨。
他閉上眼睛,俊朗而威嚴的臉上,第一次流露出近乎絕望的神情。他用只有自己才能聽見的聲音喃喃自語:「難道,真是天要亡他,也要斷朕一臂嗎……」
殿外的寒風發出嗚嗚的呼嘯,穿過宮殿的飛檐斗拱,像是遠方傳來的一曲悲歌,仿佛在提前為一位即將逝去的大明忠臣送行。
故事的氣氛,在此刻,已然降至冰點。
04
就在大政殿內一片死寂,皇太極心灰意冷,幾乎就要接受洪承疇必死無疑這個結局的時候,殿外忽然傳來內侍尖細而略帶猶豫的通報聲:
「啟稟皇上……永福宮莊妃娘娘……求見。」
聲音在空曠的大殿里顯得格外突兀。
皇太極緩緩睜開眼睛,眉頭立刻擰成了一個疙瘩。這個時候?她來做什麼?後宮的女人,在這個所有人都避之不及的時刻,突然求見,這太不尋常了。
「讓她進來。」他有些不耐煩地說道,語氣裡帶著一股尚未消散的煩躁。
片刻之後,身著一襲素雅宮裝的布木布泰,步履輕盈而沉穩地走進了大殿。她沒有像往常那樣帶著溫婉的笑容,一張秀美的臉上滿是莊重和認真。她走到殿中,對著寶座上的皇太極,行了一個標準的大禮。
「這麼晚了,你來做什麼?」皇太極看著跪在地上的布木布泰,聲音冷硬,「後宮婦人,不要干預前朝之事。朕現在……沒心情。」
這幾乎是呵斥了。這既是一個被煩心事纏身的男人的本能反應,也是一個大時代的君主對「後宮不得干政」這條鐵律的維護。
布木布泰卻沒有被這冰冷的話語嚇退。她依舊跪在地上,抬起頭,清亮的眼眸直視著皇太極,聲音柔和卻異常清晰:
「臣妾不敢幹預前朝,只是知道皇上正為洪承疇的事煩心。臣妾斗膽,想問皇上一句話。」
皇太極沒有做聲,算是默許了。
「皇上派去的那些人,無論是威逼還是利誘,歸根結底,是不是都是想讓他『投降』?」
皇太極從鼻子裡哼了一聲:「不然呢?」
「可是,」布木布泰的聲音微微提高了一些,帶著一種獨特的邏輯力量,「一個一心求死、以死為榮的人,您卻偏偏要讓他『活下來投降』。這在他自己看來,不就是要勸他背叛自己的信仰,拋棄自己的名節嗎?他怎麼可能會聽?皇上,您想得到的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可您派去的那些人,卻總想著把這柄劍強行掰彎了,還指望它能保持原有的鋒利。這……這可能嗎?」
這番新穎的比喻,讓皇太極煩亂的思緒為之一振。他那雙鷹隼般的眼睛裡,第一次在今晚,閃過一絲真正的興趣。他坐直了身子,身體微微前傾,盯著布木布泰:「那依你之見呢?」
布木布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知道最關鍵的時刻到了。她一字一頓地,說出了那個石破天驚的請求:
「請皇上……准許臣妾,去見他一面。」
「胡鬧!」
話音未落,皇太極的怒火瞬間就被點燃了!他猛地一拍扶手,站起身來,像一頭被激怒的雄獅。「簡直是胡鬧至極!你?一個女人家!大清國的側福晉,金枝玉葉,要去那晦氣沖天的囚牢里,見一個快要死的敵國降臣?還是個男人!這要是傳了出去,朕的臉面何在!我愛新覺羅家的臉面何在!滿洲的臉面何在!」
他的咆哮聲震得大殿嗡嗡作響,燭火瘋狂地跳動。這是一個丈夫的本能,一個君主的尊嚴,一個民族領袖對面子的看重,在此刻全部爆發了出來。這已經不僅僅是策略問題,而是觸及了當時社會最根本的禮教、規矩和名聲。
面對皇太極的雷霆之怒,布木布泰卻出奇地鎮定。她沒有被嚇得瑟瑟發抖,反而再次抬起頭,眼神中的堅定非但沒有減弱,反而更加明亮。
她等皇太極稍稍平息了一下怒氣,才不疾不徐地開口,條理清晰地分析起來:
「皇上,請您息怒,聽臣妾說完。」
「您先想一想,為什麼所有人都失敗了?因為您派去的,不是想從他那裡得到什麼的政敵,就是被他看不起的叛徒,再不然就是想用金錢收買他的說客。在他洪承疇的眼裡,這些人都是『外人』,都是帶著明確的目的來索取、來逼迫的。他心裡那道防線,比盛京的城牆還要厚,怎麼可能對這些人敞開?」
她停頓了一下,讓皇太極有時間消化她的話,然後繼續說道:「而臣妾,不一樣。」
「在洪承疇眼裡,我只是一個女人,一個與他素不相識、無冤無仇的後宮妃子。我不代表任何官職,也沒有任何權力上的威脅。男人和男人之間,永遠是權力的博弈,是尊嚴的對峙,是意志的比拼。但是,一個女人,尤其是臣妾這樣一個身份,出現在他面前,或許……或許能讓他卸下那身堅硬的盔甲,不再把他自己當成一個寧死不屈的『總督』,而是作為一個普通的『人』,說幾句心裡話。」
看到皇太極眼中的怒意漸漸被思索所取代,布木布泰知道自己的話起了作用。她決定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打消他最後的顧慮。
「皇上,您想,洪承疇馬上就要死了。軍醫已經斷言,他活不過今晚。您麾下的滿朝文武,所有能想到的法子都試過了,全都失敗了。可以說,我們已經山窮水盡,再也沒有什麼可輸的了。」
「就讓臣妾去試一試吧。最壞的結果,無非是和現在一樣,他還是死了,臣妾無功而返,悄悄地回來,不會有任何人知道。可是……萬一呢?萬一臣妾能讓他重新燃起一點求生的念頭,能讓他開口喝下一口水,能讓他說出一句願意為大清效力的話……那對皇上,對整個大清而言,不就是天大的意外之喜嗎?」
她的聲音充滿了蠱惑的力量:「反正已經到了絕路,為何不讓臣妾去探一探那唯一的,可能存在的『柳暗花明』呢?」
大殿里,再次陷入了長久的沉默。
皇太極高大的身影在燭光下佇立著,他死死地盯著跪在地上的布木布泰。他看到了什麼?他看到的不再是一個柔弱順從的妃子,而是一個有著敏銳洞察力、超凡勇氣的政治盟友。
她的每一句話,都像經過精心計算的棋子,精準地落在了他內心最糾結、最渴望的位置上。
他的內心在「君主的面子」和「對曠世奇才的渴望」之間劇烈地搖擺、鬥爭。
是啊,布木布泰說得對,情況已經不可能比現在更糟糕了。讓一個女人去嘗試,看似荒唐,卻又何嘗不是一個打破僵局的奇招?
良久,良久。
皇太極終於從牙縫裡擠出了幾個字,聲音艱澀而決斷:
「……好。朕就准你這一次。」
他轉過身去,背對著布木布泰,仿佛不願再看她,又像是在掩飾自己複雜的情緒。「但只有兩個時辰。天亮之前,不管成與不成,你必須給朕回來!」
他頓了頓,又從腰間解下一塊象徵著無上權力的令牌,扔在地上,發出一聲清脆的響聲。
「帶上朕的令牌,任何人不得阻攔。」
他的聲音壓低了,變得複雜難辨,仿佛還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關切。
「還有……自己當心。」
這句話里,既有君臨天下的決斷,也有一絲作為一個丈夫,對自己妻子最本能的擔憂。
布木布泰如聞天籟,她深深地叩首於地,額頭貼著冰冷的金磚。
「謝皇上隆恩!」
她拾起地上的令牌,緊緊攥在手心,然後站起身,沒有絲毫猶豫,轉身朝著殿外那深沉的夜色走去。夜風吹起了她素色的裙角,她的身影在巨大的宮殿映襯下,顯得那般單薄,卻又蘊含著一股令人心悸的、無比堅定的力量。
一場註定要被記入史冊,一場將決定歷史走向的密談,即將在一個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地方,由一個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人,拉開帷幕。
05
布木布泰沒有立刻前往那座囚籠。
她回到永福宮,並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她首先做的,是換下一身帶有宮廷氣息的綢緞宮裝,選了一套質地柔軟、顏色素凈的青灰色布衣。這身衣服,讓她看起來不像一個高高在上的貴妃,更像一個尋常人家裡知書達理的婦人。然後,她屏退了大部分宮人,只留下自己最信賴、也是從蒙古草原一同陪嫁過來的侍女蘇茉兒。
「娘娘,您這是要……」蘇茉兒看著主子這身打扮,又看著她嚴肅的神情,心中充滿了疑惑和不安。
布木布泰沒有解釋,她徑直走進了永福宮的小廚房。此刻已是深夜,廚房裡只有幾個負責守夜的廚役,看到莊妃娘娘突然駕到,一個個嚇得魂飛魄散,紛紛跪倒在地。
「都起來吧,不必聲張。」布木布泰的聲音很平靜,「把爐火生起來,再取些上好的人參和清水來。」
在眾人一片驚愕不解的目光中,布木布泰竟然親手點燃了爐火。她將切好的人參片放入瓦罐中,注滿清水,然後將瓦罐穩穩地架在爐火上。
她沒有假手於人,就那麼靜靜地守在爐火邊,看著那火焰舔舐著瓦罐的底部,聽著罐里的水漸漸發出咕嘟咕嘟的聲響。
她親自熬制這碗湯,這個行為本身就充滿了一種深沉的儀式感。她不是去「勸降」,也不是去「審問」,她是要去「探望」一個病人,一個心病入膏肓的將死之人。
她帶去的,不能是象徵權力的聖旨,也不能是象徵財富的金銀,而必須是這樣一碗能傳遞最質樸、最本原的溫暖與關懷的參湯。
湯熬好了,一股濃郁的參香在小廚房裡瀰漫開來。布木布泰小心地將參湯倒入一個白瓷碗中,再放入一個有保溫夾層的食盒裡。
她對蘇茉兒說:「你跟我來,記住,從現在開始,多看,多聽,少說話。」
蘇茉兒雖然心中驚疑不定,但還是用力點了點頭,提起了食盒。
主僕二人借著夜色的掩護,悄無聲息地離開了永登宮。深夜的皇城,寒風刺骨,吹得道旁的燈籠搖曳不定,在地上投下鬼魅般的光影。布木布泰緊了緊身上的披風,手心裡緊緊攥著那塊冰冷的令牌,內心卻是一片火熱。
當她來到城北那座戒備森嚴的院落外時,守衛的巴牙喇護軍看到兩個女人深夜到訪,立刻警惕地舉起了手中的兵器。
「來者何人!」
布木布泰沒有說話,只是從袖中取出了那塊刻著滿文的黃銅令牌。為首的護軍頭領借著燈籠的光一看,那令牌上的紋飾和刻字,讓他瞬間倒吸一口涼氣,雙腿一軟,差點跪了下去。這是皇太極從不離身的信物,見此牌如見皇上親臨!
「開……開門!」他結結巴巴地命令道,同時用眼神示意手下人全部退到一邊,不許多看,不許多問。
沉重的木門在「吱呀」聲中被打開,一股混合著霉味、草料味甚至還有一絲若有若無的死亡氣息,從院內撲面而來,讓蘇茉兒忍不住用袖子掩住了口鼻。布木布泰卻像是沒有聞到一樣,面色平靜地邁步走了進去。
在護軍的引領下,她來到那間關押著洪承疇的屋子前。一盞昏黃的油燈掛在門外,映照著那扇緊閉的房門,像一隻窺探地獄的眼睛。
「打開。」布木布泰輕聲說。
鎖鏈被嘩啦啦地取下,門被推開。裡面的景象,比想像中還要糟糕。房間狹小而陰暗,空氣污濁不堪。唯一的家具,就是一張歪歪扭扭的破桌子和幾個草墩。
而房間的角落裡,草堆之上,蜷縮著一團黑乎乎的人影,像一截被遺忘的枯木,一動不動,不知是死是活。
布木布泰讓蘇茉兒留在門口,自己提著裙擺,獨自走了進去。
她沒有像之前的那些人一樣,急著走到洪承疇面前開口說話。她的第一舉動,出乎了所有人的預料。
她先是環顧了一下這個令人窒息的小屋,然後走到那扇僅有的、糊著厚厚窗紙的小窗前。她伸出自己那雙保養得宜的纖纖玉手,用衣袖,輕輕地、仔細地,擦拭著窗紙上積滿的灰塵與污垢。隨著她的動作,一層層的塵埃被拭去,窗紙變得透亮了一些。恰好此時,一片雲彩飄過,一縷清冷的月光,透過那片被擦拭乾凈的窗紙,悄然無聲地照了進來,在地上投下了一小塊銀白色的光斑。
這一個小小的舉動,仿佛給這個密不透風的死亡空間,帶來了一絲微弱的生機。
接著,布木布泰走到那張破桌前,讓蘇茉兒將食盒放了上去。她打開食盒,將那碗還冒著絲絲熱氣的參湯端了出來。濃郁而溫暖的參香味,立刻在這片污濁的空氣中擴散開來,霸道地驅散了部分霉味。
她做完這一切,依舊沒有開口。她端著那碗湯,沒有直接送到洪承疇面前,只是走到了離他三四步遠的地方,將湯碗輕輕地放在了地上。然後,她就在旁邊一個還算乾淨的草墩上,靜靜地坐了下來,雙手交疊放在膝上,一言不發。
時間,在這一刻仿佛凝固了。
牢房裡,只聽得見外面護軍們偶爾走動的腳步聲,風吹過屋檐的嗚咽聲,以及……布木布泰和角落裡那個人影之間,兩種截然不同的呼吸聲。一個平穩而悠長,一個微弱而斷續。
洪承疇依然背對著她,像一座沒有生命的雕塑。但如果有人能靠近看,會發現他那蜷縮的身體,似乎比剛才更加僵硬了。他能感覺到背後有人,能聞到那久違的、帶著暖意的食物香氣。但他想不通,來的是誰?為什麼不說話?
一個尊貴的、帶著侍女、能命令皇上親兵的女人,深夜來到這必死之地,不威逼,不勸誘,只是擦了扇窗,放下一碗湯,然後就這麼靜靜地坐著。
這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難以言喻的心理壓迫,更勾起了他心中一絲幾乎已經泯滅的好奇。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久到蘇茉兒都覺得自己的腿有些發麻了。她焦急地看著自家主子,不明白她葫蘆里到底賣的什麼藥。
就在這令人窒息的沉默中,布木布泰終於開口了。
她的聲音很輕,很柔,像是怕驚擾了這屋裡某個沉睡的精靈,又像是怕這聲音太過突兀,會刺痛一個久處黑暗之人的耳朵。
她沒有說「洪將軍」,更沒有說「皇上讓我來的」。她只是望著地上那碗漸漸失去熱氣的參湯,仿佛在自言自語,又仿佛在對一個許久未見的老朋友閒話家常:
「天,真冷啊。我從一些從關內來的商人那裡聽說,你們南方的冬天,是不下雪的吧?尤其……是福建泉州那邊。想來,那裡的冬天應該也是濕冷的,就像這碗參湯,若是再放一會兒,等到它徹底涼透了,怕是就再也暖不了人的心了。」
這句話,如同一顆投入死水潭的小石子,無聲無息,卻激起了一圈圈深入底部的漣漪。
「福建泉州」——這四個字,像一把失傳已久的鑰匙,在洪承疇那早已被恥辱和絕望銹死的腦海深處,「咔嗒」一聲,精準地插入了那把塵封的心鎖。
他的身體,幾不可察地猛地一顫。這是這麼多天以來,他第一次對外界的刺激,做出如此清晰的反應。
但他依然沒有回頭,也沒有說話。黑暗中,沒人能看清他此刻的表情。
布木布泰也沒有繼續說下去。她再次陷入了沉默,似乎在耐心等待著那把鑰匙,慢慢地轉動。牢房裡的氣氛,比剛才更加詭異和緊張。她像一個最高明的漁夫,已經撒下了網,現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魚兒自己掙扎著入網。
地上的那碗參湯,最後一絲熱氣也散盡了。蘇茉兒看著自家主子,眼中寫滿了焦急,她用眼神催促著,仿佛在說:娘娘,快說點什麼吧!時間不多了!
就在蘇茉兒都以為這次不同尋常的嘗試,終究也要和其他人一樣以失敗告終時,那個蜷縮在草堆里的身影,終於,動了。
他沒有回頭。
他只是用一種極其嘶啞、微弱,如同兩片砂紙在互相摩擦的聲音,從喉嚨的深處,擠出了一個讓布木布泰都感到萬分意外的問題。
他問的不是「你是誰」,也不是「你來做什麼」,更不是讓她「滾開」。
而是——
「你……見過樑上的那隻燕子嗎?它今天……有沒有回來?」
話音剛落,本章結束。這句莫名其妙的話,像一道謎題,橫亘在死寂的牢房之中。他究竟是因飢餓而神志不清,說起了胡話?還是在用一種無人能懂的暗語,進行著最後的試探?這隻神秘的「燕子」,到底是什麼?這個巨大的、匪夷所思的懸念,將牢牢地抓住每一個人的心,迫使他們瘋狂地想要知道,布木布泰將如何應對這個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開局。
06
蘇茉兒聽到這個問題,整個人都懵了。燕子?這冰天雪地的隆冬時節,哪裡來的燕子?她下意識地抬起頭,看了看光禿禿的、結著蛛網的房梁,心裡只有一個念頭:這洪承疇,果然是餓得發了瘋,開始說胡話了。她緊張地看向布木布泰,不知主子該如何接下這句瘋話。
然而,布木布泰的臉上卻毫無意外之色。當聽到「燕子」兩個字時,她的心反而徹底定了下來。她的嘴角,甚至在無人察覺的黑暗中,勾起了一抹瞭然的微笑。
賭對了。
她來之前做的那些看似無用的功課,在這一刻,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她曾通過那個小太監,搜集了所有能找到的,關於洪承疇的軼事。其中有一條就記載著:洪承疇在總督薊遼軍務時,官署大堂的房樑上有一窩燕子。
有一次,燕子受了驚,他為此大發雷霆,甚至責罰了手下的吏員。此事後來被當成一樁趣聞,用以證明他這位鐵血將帥,也有著「愛惜生靈」的仁慈一面。
所以布木布泰瞬間就明白了,洪承疇此刻問的,根本不是什麼真正的燕子。這隻「燕子」,是他內心世界裡一個極其微弱、卻又無比重要的象徵。它象徵著他對「生」的一絲留戀,象徵著他作為一個讀書人心中那點尚未泯滅的「善」與「仁」,象徵著他即便身處絕境,也還在意著那些微小而美好的事物。
他不是在說胡話。他是在用一種極為隱晦、也極為驕傲的方式進行試探。他在問:你,懂我嗎?你究竟是又一個把我當成獵物和工具的說客,還是一個能看透我這身硬殼,看到我內心深處那點柔軟的知己?
這個問題,是最後一道防線,也是唯一的門徑。答對了,門便開了;答錯了,門將永遠關閉。
布木布泰沒有直接回答「有」或者「沒有」。她緩緩站起身,走到那碗已經冰涼的參湯前,彎腰將其端了起來。這個動作,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洪承疇的注意力,儘管他沒有回頭,但他的耳朵一定在聽著。
她走到門口,將那碗涼透了的湯遞給蘇茉兒,輕聲吩咐道:「去,再為將軍熱一碗來。」
做完這一切,她才重新走回草墩邊坐下,目光仿佛穿透了牆壁,望向了外面漆黑的夜空。她用一種帶著些許悵惘和憐惜的語氣,悠悠地說道:
「將軍,外面的風太大了,天也太冷了。樑上的燕子是聰明的鳥兒,它早就帶著一家老小,飛到南方溫暖的地方去過冬了。」
她的聲音頓了頓,仿佛給了洪承疇一個喘息和思考的空間,然後才繼續說下去,聲音裡帶著一層溫柔的喻意:
「它若還傻傻地留在這裡,不肯離去,那結果只有一個,就是和您一樣,在這絕望的寒冬里,活活地凍死、餓死。有時候……暫時的離開,並不是背叛,而是為了等到下一個春天,能夠更好地歸來,重新銜泥築巢啊。」
一番話,舉重若輕。她既無比精準地回答了他的問題,又巧妙地將「燕子」的意象,與他洪承疇自身的處境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她沒有勸他「投降」,而是在告訴他「求生」。她將「投降」這個恥辱的字眼,偷換成了「暫時的離開」和「等待春天」,這其中不帶任何強迫,卻充滿了哲理和人情味。
角落裡,那具僵硬的身體再次劇烈地一震。這一次的震動,比上一次更為明顯。
黑暗中,傳來一陣悉悉索索的響聲。洪承疇,那個幾十天來始終背對眾人,如同石化了一般的男人,竟然緩緩地,用一種極其艱難、仿佛每動一下骨頭都在呻吟的動作,轉過了他的頭。
他第一次,正眼看向了這個深夜來訪的女人。
油燈的光芒從門口斜射進來,只能照亮布木布泰的側臉。他看不清她的全貌,只能看到一個年輕的、柔和的輪廓,和一雙在昏暗中依舊閃爍著智慧與真誠光芒的眼睛。那雙眼睛裡,沒有貪婪,沒有算計,沒有逼迫,只有平靜的關切和深深的理解。
這個女人,懂他。
這個念頭,像一道閃電,劈開了洪承疇心中混沌的黑暗。幾十天了,這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懂他的人。
布木布泰沒有被他那張形同鬼魅的臉嚇到。她迎著他審視的目光,微微頷首,算是打了招呼。然後,她便不再看他,而是自顧自地,聊起了一些看似完全無關緊要的事情。
「聽那些商人說,將軍的家鄉泉州,是個頂好頂好的地方。那裡有個叫刺桐港的,幾百年前就是天底下最熱鬧的港口,世界各地的船都往那裡跑。」
「他們還說,泉州人最愛喝一種茶,叫功夫茶。用很小的茶杯,喝起來特別講究,能品出人生的千百種滋味。想來,那茶的味道,一定能解鄉愁吧。」
她就像一個普通的鄰家女子,在與人閒話家常。她說的每一句話,都像一片溫暖的羽毛,輕輕地,拂過洪承疇心中最柔軟、最敏感的地方。家鄉、港口、功夫茶……
這些遙遠而親切的意象,喚醒了他被囚禁已久的記憶,讓他暫時忘記了自己是個階下囚,而重新記起,他還是那個來自福建南安的讀書人。
更讓他感到震驚的是,布木布泰竟然聊起了他年輕時寫的一首詩。
「臣妾偶然間讀到將軍早年所作的一首七律,其中一句『仗劍還須學冠軍,磨盾終見枕戈人』,真是豪情萬丈。可後面那句『故園楊柳依依在,何日東風送我還』,又充滿了文人的細膩與感傷。臣妾當時就在想,能寫出這樣詩句的人,一定是個心中既有金戈鐵馬,又有綠柳江南的奇男子。」
洪承疇的眼眶,猛地一熱。那幾乎已經乾涸的淚腺,竟然有了一絲濕意。
他的詩!連他自己都快要忘記的少年之作,竟然被一個身在盛京深宮裡的異族女子,記得如此清楚,還品讀得如此透徹!
他那顆早已沉入死水的心,開始不由自主地跳動起來。這幾十天,所有人都把他當成一扇需要撞開的門,只有眼前這個女人,把他當成一本需要細細品讀的書。
這種被理解、被尊重、被當成「知己」的感覺,是他在這冰冷的清營里,從未體會過的溫暖。他那道堅不可摧的心理防線,在金錢、地位、酷刑、親情牌面前都毫髮無損,此刻,卻在這看似無力的溫言軟語之中,悄然出現了一道真正的、深刻的裂縫。
就在這時,蘇茉兒端著第二碗熱氣騰騰的參湯走了進來。這一次,她將湯碗直接放在了洪承疇的面前。
洪承疇的喉結,不受控制地上下滾動了一下。
他終於開口了。聲音依然沙啞得厲害,但不再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冰冷,而是帶著一絲遲疑和探究。
「你……究竟是誰?」
07
牢房裡的氣氛,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當洪承疇問出「你是誰」這個問題時,就代表著他已經從一個完全封閉的自我世界裡,探出了一個頭。他開始對外界產生好奇,開始願意進行一場真正的對話。
布木布泰知道,攻心之戰,已經取得了第一階段的勝利。現在,是時候進入最核心、最關鍵的環節了。
她沒有直接回答自己的身份,因為「莊妃」這個名號,只會重新將他們拉回君臣、敵我的對立面。她只是平靜地看著他的眼睛,用一種更加嚴肅和懇切的語氣說道:
「我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一個敬佩將軍忠義的人。」
她先是毫不吝嗇地給予了對方最高的肯定和尊重。「將軍被俘至今,一心求死,為的是全大明之忠,報崇禎皇帝知遇之恩。這份風骨,這份氣節,天下誰人能不敬佩?我雖是一介女流,也發自內心地敬佩您。」
這番話,讓洪承疇緊繃的神經稍稍放鬆了一些。對方沒有像其他人一樣,一上來就否定他的價值觀,指責他「不識時務」,這讓他感覺到了被尊重。
然而,布木布泰的話鋒,緊接著便是一個凌厲無比的轉折。她拋出了一個他從未思考過,也足以顛覆他整個信仰體系的顛覆性問題:
「可是,將軍,您有沒有想過。您的這份『忠』,究竟是忠於那個氣數將盡、風雨飄搖的朱家王朝,還是……忠於這天底下千千萬萬,正在戰火中苦苦掙扎的黎民百姓?」
這句話,如同一道驚雷,在洪承च्यू那虛弱卻依舊高傲的腦海中轟然炸響!
忠於百姓?
他愣住了,嘴唇微微張開,卻發不出任何聲音。這個概念,對他這個浸淫儒家經典數十年的傳統士大夫來說,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古訓,陌生的是,他從未想過,有一天「忠君」和「忠民」會成為一道需要他做出抉擇的題目。
布木布泰沒有給他太多震驚的時間,她乘勝追擊,將這個論點層層深入地剖析開來,聲音不高,卻字字句句都像重錘,敲打在洪承疇的心坎上。
「將軍請看今日之天下!關內,流寇四起,李自成、張獻忠之流,所過之處,赤地千里,百姓流離失所,易子而食,其狀之慘,不忍卒睹!關外,我大清兵鋒正盛,入主中原已是早晚之事。大明江山,實際上早已是千瘡百孔,分崩離析。」
「在這種情勢下,將軍您若一死了之,確實,您成全了您個人的千秋名節,史書上會記下『洪承疇兵敗殉國』這幾個字。可是,然後呢?」
她身體微微前傾,目光灼灼地盯著他:「然後,您這一身匡時濟世的驚天緯地之才,您這滿腹可以安邦定國的良謀大策,難道就要隨著您這副枯骨,一同被埋入這北地的黃土之下嗎?!」
「將軍想一想,當初崇禎皇帝提拔您,重用您,將大明最精銳的部隊交給您,他所期望的,難道僅僅是您為他朱家一人一姓去死嗎?不!他期望的,是您能用您的才華和能力,為他掃平流寇,抵禦外敵,還天下一個太平,讓黎民百姓能夠安居樂業!」
「如今,雖然君主可能要換了,但這天下,還是那個天下;這天下的百姓,還是那些無辜的百姓!一個真正的忠臣,他的『小忠』,是忠於某一個君主;而他的『大忠』,最終應該是忠於天下蒼生,忠於這片土地上所有的生靈啊!」
洪承疇的呼吸變得急促起來。布木布泰的話,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精準地切開了他用「忠君」理念構築的堅固堡壘,讓他看到了一個更宏大,也更具責任感的圖景。
他想起了自己從北京一路領兵至松山的沿途所見。那些面黃肌瘦的災民,那些倒在路邊的餓殍,那些因為戰亂而破碎的家庭,一幕一幕,重新在他眼前浮現。他當初手握重兵,最大的願望,不正是要結束這一切嗎?
布木布泰的聲音變得更加柔和,也更加具有穿透力。
「求死,是一件容易的事。眼睛一閉,牙一咬,所有痛苦、所有掙扎、所有罵名,就都與您無關了。那是解脫。」
「可是,求生,並且是背負著『變節』『投降』的千古罵名去求生,去利用敵人的力量,去完成自己未竟的抱負,去親手結束這場讓億萬生靈塗炭的戰亂……那才是更需要巨大勇氣和擔當的艱難選擇啊!」
「將軍,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留得您這有用之身,將來無論是輔佐新君,制定善待漢人的策略,還是獻計獻策,早日平定天下,讓百姓們能少流一些血,早一天吃上一口飽飯。這……難道不是一種更高層次,也更具意義的『盡忠』嗎?」
一番話,擲地有聲,振聾發聵。
布木布泰沒有試圖去撲滅洪承疇心中的「忠義之火」,恰恰相反,她用一種全新的方式,為這團火焰找到了一個更宏大、更光明的燃燒方向。她沒有否定他的過去,而是為他的未來,提供了一個可以被他自己內心所接受的,全新的道德台階。
洪承疇的世界觀,在這一刻,發生了劇烈的動搖,甚至可以說是崩塌與重建。他一直以來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信條所禁錮,將個人的氣節看得比什麼都重。但布木布泰卻為他打開了另一扇窗戶,窗外,是他曾經發誓要拯救的,水深火熱中的天下蒼生。
是選擇成就個人的「忠烈」之名,然後任由天下繼續糜爛?還是選擇背負萬世的罵名,卻能有機會親手去實現「兼濟天下」的政治抱負?
這個選擇題,太過艱難,也太過沉重。他的內心,掀起了滔天海嘯。堅守了半生的信仰,與一個更加宏大的人道主義理想,在他的腦海中激烈地交戰著。他那張乾枯的臉上,肌肉不住地抽搐,眼神中充滿了痛苦、迷茫和劇烈的掙扎。
08
看著洪承疇眼中那片翻江倒海的掙扎,布木布泰知道,他那堅固的信仰堤壩已經出現了無數裂痕,距離徹底決堤,只差最後一股推力。
她沒有再用那些宏大的道理去衝擊他,而是從袖中,緩緩地取出了一件東西——一面製作精巧的,可以隨身攜帶的銅柄小鏡子。這是後宮女子常用的物件,此刻卻成了她最後的,也是最厲害的武器。
她將鏡子遞到洪承疇的面前,鏡面正對著他的臉。她的聲音,也從剛才的慷慨激昂,轉為一種帶著無限憐憫的輕柔。
「將軍,您看看您自己。您看看鏡子裡的這個人。」
洪承疇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那片小小的、光亮的鏡面上。
鏡子裡,是一張怎樣可怕的臉啊!頭髮像一叢枯草,鬍子拉碴,糾結成團。眼窩深陷,如同兩個黑洞。嘴唇乾裂,布滿了血口。整張臉頰沒有一絲血色,只剩下一層蠟黃的、緊緊包裹著骨頭的皮膚。這哪裡還是當初那個意氣風發、統領十三萬大軍的薊遼總督?這分明就是一個從地獄裡爬出來的,形容枯槁、不成人形的餓鬼。
他自己的模樣,讓他自己都感到一陣心驚。
布木布泰的聲音,適時地在他耳邊響起,像一聲溫柔的嘆息:
「將軍,您一心求死,可您想過沒有,您遠在福建南安家中的那位老母親……她若是看到您如今這副模樣,是會為您所謂的『盡忠殉國』而感到欣慰,還是會為白髮人送黑髮人而肝腸寸斷、哭瞎了雙眼?」
「老母親」這三個字,如同一柄最沉重的巨錘,毫無花哨地,狠狠地砸在了洪承疇內心最柔軟、最脆弱的地方。
「聖人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布木布泰的聲音,仿佛帶著一種魔力,每一個字都清晰地鑽進他的心裡,「您為了君主盡了愚忠,卻要陷自己的母親於不孝、不慈的萬劫不復之地。讓她在晚年,不僅要承受喪子之痛,還要承受因您『叛國』被俘而可能帶來的種種牽連……將軍,這,真的是您想要的『全節』嗎?」
「忠」與「孝」,自古以來就是懸在所有中國讀書人頭上的兩座大山。當它們不衝突時,便是完美的道德楷模;當它們發生劇烈衝突時,足以讓任何一個鐵漢崩潰。
在此之前,洪承疇認為「忠」大於「孝」,為國盡忠,便是最大的孝。但布木布泰卻為他展示了另一面:你死了,你的「忠」結束了,可你留給母親的「不孝」之痛,卻是永無止境的。你的死,是一種自私的成全,卻是對母親最殘忍的拋棄。
對君主的忠誠,在這一刻,與對母親最本原的牽掛和愧疚,與對天下蒼生的責任感,這三股力量交織在一起,終於壓垮了他心中那根名為「愚忠」的最後的稻草。
他緩緩地抬起頭,目光從那面讓他自己都感到陌生的鏡子上移開,落在了面前那碗早已不再滾燙,卻依舊散發著溫暖氣息的參湯上。
他看著湯,又看看眼前這位比自己小了將近二十歲,看似柔弱,卻有著驚人智慧和深刻洞察力的年輕女子。她不是來勸降的魔鬼,她分明是來點醒他,渡他出這無間地獄的菩薩。
長久的,死一般的沉默。
牢房裡,只聽得到洪承疇那愈發粗重的呼吸聲。
終於,他那隻如同枯枝般的手,顫抖著,緩緩地伸了出來,伸向了那隻白瓷碗。他的動作很慢,很艱難,仿佛用盡了畢生的力氣。
他端起了那碗湯。
然後,在布木布泰平靜的注視下,他仰起頭,將那碗凝聚了希望、理由和新生的參湯,一飲而盡。
這是他被俘數十日以來,第一次主動進食。
湯水入喉,仿佛一股暖流,瞬間流遍了他那幾近乾涸的四肢百骸。身體上的暖意,點燃了心理上的生機。
他放下空碗,那雙已經有了些許神采的眼睛,深深地看著布木布泰。然後,他掙扎著,挪動著自己僵硬的身體,對著眼前這個女子,緩緩地,鄭重地,跪了下去。
這個跪,不是對一個妃子的跪拜,而是一個迷途之人,對指引他方向的「知己」的感謝。
他沙啞地開口,說出了那句徹底改變了他自己,也深刻影響了未來歷史走向的話:
「罪臣……洪承疇……但求速見大清皇帝。另……另請……為我剃髮。」
剃髮易服,這是投降歸順最徹底、最無可辯駁的象徵。從說出這句話的這一刻起,大明的薊遼總督洪承疇,已經死了。活下來的,將是大清的臣子,洪承疇。
天色微明,當第一縷晨曦刺破盛京上空的黑暗時,布木布泰裹緊披風,平靜地走出了那座院落。她的臉上看不出喜悅,也看不出疲憊,只有一種如深潭般的沉靜。
不久之後,整個大清朝堂都為之震動。
那個寧死不屈、水米不進的硬骨頭洪承疇,在沐浴更衣之後,剃去了他珍視的髮髻,換上了滿洲官員的服飾,精神抖擻地出現在了皇太極的面前,叩首稱臣。
滿朝文武,尤其是那些輪番上陣卻屢屢碰壁的漢臣和滿洲親貴,一個個都目瞪口呆,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們絞盡了腦汁,也想不明白,就在那個所有人都以為洪承疇必死無疑的夜晚,那個年輕美貌的莊妃,在那個陰暗的密室里,在那短短的幾個小時之內,究竟對他施了什麼樣的魔法?
大政殿之上,皇太極在接受了洪承疇的跪拜,並授予他高官厚祿之後,目光越過歡欣鼓舞的群臣,望向了遠遠站在後宮嬪妃人群之中的布木布泰。她依舊是那副恬靜淡然、與世無爭的模樣,仿佛昨夜那場驚心動魄的博弈與她毫無關係。
但皇太極的心中卻雪亮。他知道,從今夜起,他不僅得到了一個能為他打開中原大門的洪承疇,更重要的是,他重新認識了自己身邊這位來自科爾沁草原的妃子。她擁有的,不僅僅是美貌,更是一種足以影響國運的、深不可測的政治智慧。
數日後,已經恢復了昔日幾分神采的洪承疇,身著嶄新的大清官服,獨自一人登上了盛京的城樓。
他憑欄遠眺,望著南方那片他曾經浴血守護,如今卻已成故國的土地,眼神複雜無比。寒風吹動著他額前那根金錢鼠尾辮,也吹起了他心中的萬千思緒。
他知道,從今往後,他將永遠地背負「漢奸」「叛徒」的千古罵名。但他心中,也燃起了一團全新的火焰。那是在那個寒冷的夜晚,由一個女人為他親手點燃的——那是「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更宏大的責任之火。
沒有人用刀劍逼迫他,沒有人用金銀誘惑他。
孝莊,那個年僅二十餘歲的女子,她只是用一個女人的細膩,和一種超越常人的智慧,看穿了一個男人的驕傲,讀懂了一個文人的掙扎,解構了一個忠臣的信仰。
然後,她又親手為他重塑了一個可以讓他自己說服自己,並昂首活下去的理由。她讓他深刻地明白:有時候,苟且地活著,比壯烈地死去,需要更大的勇氣,也蘊含著更深遠的價值。
這,就是那數小時密談中,真正的不傳之秘。
這個提議立刻在朝堂上引發了軒然大波。
「萬萬不可!」范文程第一個站出來,跪倒在地,幾乎是聲淚俱下,「皇上!此乃取死之道啊!洪承疇以忠孝立身,我們若以其母脅之,是逼他陷入忠孝不能兩全的絕境。到時候,他不但不會降,反而會立刻求死,以全孝道,免使其母受辱!此其一。其二,此舉一旦傳開,天下漢人會如何看我大清?會認為我大清乃是不顧人倫、行事卑劣的虎狼之邦!到那時,只會激起關內軍民更強烈的抵抗之心,天下所有有才之士,誰還敢歸附我大清?此舉是得一洪承疇之屍,而失盡天下之心啊!請皇上三思!」
「范大人此言差矣!」另一位滿洲將領反駁道,「婦人之仁!咱們打天下,靠的是刀把子,不是筆桿子!不給他們點顏色看看,他們永遠不知道誰才是主子!」
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在大殿內激烈地交鋒,一方主張鐵血手腕,一方主張攻心為上。皇太極坐在高高的龍椅上,聽著下面的爭吵,只覺得頭痛欲裂。他高大的身軀深深地陷在寶座里,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無力。
他既渴望得到洪承疇這把能打開中原大門的鑰匙,又深刻地明白范文程所說的政治後果。他不是一個只懂得殺戮的莽夫,他有著更宏大的政治抱負,他要的是整個天下,是人心所向。他的威嚴、他的智慧、他的寬宏,在洪承疇這塊沉默的頑石面前,仿佛統統失去了效用。
整個清廷上層,都被一種無計可施的陰雲所籠罩。
洪承疇的生死,已經超越了他個人,成了一個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的事件。
如果他就這麼餓死了,傳出去,就是他皇太極「德」不能感化明朝重臣,這對於一個意圖「以德服人」、取代大明正統的的政權來說,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污點和打擊。
這種集體性的挫敗感,達到了頂峰。它也為後續一個完全意想不到的人物的出場,營造了一個「非她不可」的絕望舞台。當所有的男人,無論是智者還是勇士,都宣告失敗之後,一個女人的登場,才更具石破天驚的戲劇性。
這天傍晚,軍醫送來了最後一次稟報。
「皇上……洪大人他……脈象微弱,氣息遊絲,瞳孔已經開始渙散……依微臣看,恐怕……恐怕撐不過今晚子時了。」
這個消息,如同一記重錘,徹底擊碎了皇太極心中最後一絲希望。他頹然地癱坐在龍椅上,沉默了許久,然後無力地揮了揮手,聲音里充滿了疲憊:「都退下吧……讓朕一個人靜一靜。」
大臣們躬身告退,沉重的腳步聲在空曠的大殿里漸行漸遠。很快,整個大殿里只剩下皇太極一個人。
窗外,天色已經完全暗了下來,殿內的燭火被穿堂風吹得搖曳不定,將他巨大的身影投射在冰冷的金磚上,拉得很長,很孤獨。
他閉上眼睛,俊朗而威嚴的臉上,第一次流露出近乎絕望的神情。他用只有自己才能聽見的聲音喃喃自語:「難道,真是天要亡他,也要斷朕一臂嗎……」
殿外的寒風發出嗚嗚的呼嘯,穿過宮殿的飛檐斗拱,像是遠方傳來的一曲悲歌,仿佛在提前為一位即將逝去的大明忠臣送行。
故事的氣氛,在此刻,已然降至冰點。
04
就在大政殿內一片死寂,皇太極心灰意冷,幾乎就要接受洪承疇必死無疑這個結局的時候,殿外忽然傳來內侍尖細而略帶猶豫的通報聲:
「啟稟皇上……永福宮莊妃娘娘……求見。」
聲音在空曠的大殿里顯得格外突兀。
皇太極緩緩睜開眼睛,眉頭立刻擰成了一個疙瘩。這個時候?她來做什麼?後宮的女人,在這個所有人都避之不及的時刻,突然求見,這太不尋常了。
「讓她進來。」他有些不耐煩地說道,語氣裡帶著一股尚未消散的煩躁。
片刻之後,身著一襲素雅宮裝的布木布泰,步履輕盈而沉穩地走進了大殿。她沒有像往常那樣帶著溫婉的笑容,一張秀美的臉上滿是莊重和認真。她走到殿中,對著寶座上的皇太極,行了一個標準的大禮。
「這麼晚了,你來做什麼?」皇太極看著跪在地上的布木布泰,聲音冷硬,「後宮婦人,不要干預前朝之事。朕現在……沒心情。」
這幾乎是呵斥了。這既是一個被煩心事纏身的男人的本能反應,也是一個大時代的君主對「後宮不得干政」這條鐵律的維護。
布木布泰卻沒有被這冰冷的話語嚇退。她依舊跪在地上,抬起頭,清亮的眼眸直視著皇太極,聲音柔和卻異常清晰:
「臣妾不敢幹預前朝,只是知道皇上正為洪承疇的事煩心。臣妾斗膽,想問皇上一句話。」
皇太極沒有做聲,算是默許了。
「皇上派去的那些人,無論是威逼還是利誘,歸根結底,是不是都是想讓他『投降』?」
皇太極從鼻子裡哼了一聲:「不然呢?」
「可是,」布木布泰的聲音微微提高了一些,帶著一種獨特的邏輯力量,「一個一心求死、以死為榮的人,您卻偏偏要讓他『活下來投降』。這在他自己看來,不就是要勸他背叛自己的信仰,拋棄自己的名節嗎?他怎麼可能會聽?皇上,您想得到的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可您派去的那些人,卻總想著把這柄劍強行掰彎了,還指望它能保持原有的鋒利。這……這可能嗎?」
這番新穎的比喻,讓皇太極煩亂的思緒為之一振。他那雙鷹隼般的眼睛裡,第一次在今晚,閃過一絲真正的興趣。他坐直了身子,身體微微前傾,盯著布木布泰:「那依你之見呢?」
布木布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知道最關鍵的時刻到了。她一字一頓地,說出了那個石破天驚的請求:
「請皇上……准許臣妾,去見他一面。」
「胡鬧!」
話音未落,皇太極的怒火瞬間就被點燃了!他猛地一拍扶手,站起身來,像一頭被激怒的雄獅。「簡直是胡鬧至極!你?一個女人家!大清國的側福晉,金枝玉葉,要去那晦氣沖天的囚牢里,見一個快要死的敵國降臣?還是個男人!這要是傳了出去,朕的臉面何在!我愛新覺羅家的臉面何在!滿洲的臉面何在!」
他的咆哮聲震得大殿嗡嗡作響,燭火瘋狂地跳動。這是一個丈夫的本能,一個君主的尊嚴,一個民族領袖對面子的看重,在此刻全部爆發了出來。這已經不僅僅是策略問題,而是觸及了當時社會最根本的禮教、規矩和名聲。
面對皇太極的雷霆之怒,布木布泰卻出奇地鎮定。她沒有被嚇得瑟瑟發抖,反而再次抬起頭,眼神中的堅定非但沒有減弱,反而更加明亮。
她等皇太極稍稍平息了一下怒氣,才不疾不徐地開口,條理清晰地分析起來:
「皇上,請您息怒,聽臣妾說完。」
「您先想一想,為什麼所有人都失敗了?因為您派去的,不是想從他那裡得到什麼的政敵,就是被他看不起的叛徒,再不然就是想用金錢收買他的說客。在他洪承疇的眼裡,這些人都是『外人』,都是帶著明確的目的來索取、來逼迫的。他心裡那道防線,比盛京的城牆還要厚,怎麼可能對這些人敞開?」
她停頓了一下,讓皇太極有時間消化她的話,然後繼續說道:「而臣妾,不一樣。」
「在洪承疇眼裡,我只是一個女人,一個與他素不相識、無冤無仇的後宮妃子。我不代表任何官職,也沒有任何權力上的威脅。男人和男人之間,永遠是權力的博弈,是尊嚴的對峙,是意志的比拼。但是,一個女人,尤其是臣妾這樣一個身份,出現在他面前,或許……或許能讓他卸下那身堅硬的盔甲,不再把他自己當成一個寧死不屈的『總督』,而是作為一個普通的『人』,說幾句心裡話。」
看到皇太極眼中的怒意漸漸被思索所取代,布木布泰知道自己的話起了作用。她決定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打消他最後的顧慮。
「皇上,您想,洪承疇馬上就要死了。軍醫已經斷言,他活不過今晚。您麾下的滿朝文武,所有能想到的法子都試過了,全都失敗了。可以說,我們已經山窮水盡,再也沒有什麼可輸的了。」
「就讓臣妾去試一試吧。最壞的結果,無非是和現在一樣,他還是死了,臣妾無功而返,悄悄地回來,不會有任何人知道。可是……萬一呢?萬一臣妾能讓他重新燃起一點求生的念頭,能讓他開口喝下一口水,能讓他說出一句願意為大清效力的話……那對皇上,對整個大清而言,不就是天大的意外之喜嗎?」
她的聲音充滿了蠱惑的力量:「反正已經到了絕路,為何不讓臣妾去探一探那唯一的,可能存在的『柳暗花明』呢?」
大殿里,再次陷入了長久的沉默。
皇太極高大的身影在燭光下佇立著,他死死地盯著跪在地上的布木布泰。他看到了什麼?他看到的不再是一個柔弱順從的妃子,而是一個有著敏銳洞察力、超凡勇氣的政治盟友。
她的每一句話,都像經過精心計算的棋子,精準地落在了他內心最糾結、最渴望的位置上。
他的內心在「君主的面子」和「對曠世奇才的渴望」之間劇烈地搖擺、鬥爭。
是啊,布木布泰說得對,情況已經不可能比現在更糟糕了。讓一個女人去嘗試,看似荒唐,卻又何嘗不是一個打破僵局的奇招?
良久,良久。
皇太極終於從牙縫裡擠出了幾個字,聲音艱澀而決斷:
「……好。朕就准你這一次。」
他轉過身去,背對著布木布泰,仿佛不願再看她,又像是在掩飾自己複雜的情緒。「但只有兩個時辰。天亮之前,不管成與不成,你必須給朕回來!」
他頓了頓,又從腰間解下一塊象徵著無上權力的令牌,扔在地上,發出一聲清脆的響聲。
「帶上朕的令牌,任何人不得阻攔。」
他的聲音壓低了,變得複雜難辨,仿佛還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關切。
「還有……自己當心。」
這句話里,既有君臨天下的決斷,也有一絲作為一個丈夫,對自己妻子最本能的擔憂。
布木布泰如聞天籟,她深深地叩首於地,額頭貼著冰冷的金磚。
「謝皇上隆恩!」
她拾起地上的令牌,緊緊攥在手心,然後站起身,沒有絲毫猶豫,轉身朝著殿外那深沉的夜色走去。夜風吹起了她素色的裙角,她的身影在巨大的宮殿映襯下,顯得那般單薄,卻又蘊含著一股令人心悸的、無比堅定的力量。
一場註定要被記入史冊,一場將決定歷史走向的密談,即將在一個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地方,由一個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人,拉開帷幕。
05
布木布泰沒有立刻前往那座囚籠。
她回到永福宮,並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她首先做的,是換下一身帶有宮廷氣息的綢緞宮裝,選了一套質地柔軟、顏色素凈的青灰色布衣。這身衣服,讓她看起來不像一個高高在上的貴妃,更像一個尋常人家裡知書達理的婦人。然後,她屏退了大部分宮人,只留下自己最信賴、也是從蒙古草原一同陪嫁過來的侍女蘇茉兒。
「娘娘,您這是要……」蘇茉兒看著主子這身打扮,又看著她嚴肅的神情,心中充滿了疑惑和不安。
布木布泰沒有解釋,她徑直走進了永福宮的小廚房。此刻已是深夜,廚房裡只有幾個負責守夜的廚役,看到莊妃娘娘突然駕到,一個個嚇得魂飛魄散,紛紛跪倒在地。
「都起來吧,不必聲張。」布木布泰的聲音很平靜,「把爐火生起來,再取些上好的人參和清水來。」
在眾人一片驚愕不解的目光中,布木布泰竟然親手點燃了爐火。她將切好的人參片放入瓦罐中,注滿清水,然後將瓦罐穩穩地架在爐火上。
她沒有假手於人,就那麼靜靜地守在爐火邊,看著那火焰舔舐著瓦罐的底部,聽著罐里的水漸漸發出咕嘟咕嘟的聲響。
她親自熬制這碗湯,這個行為本身就充滿了一種深沉的儀式感。她不是去「勸降」,也不是去「審問」,她是要去「探望」一個病人,一個心病入膏肓的將死之人。
她帶去的,不能是象徵權力的聖旨,也不能是象徵財富的金銀,而必須是這樣一碗能傳遞最質樸、最本原的溫暖與關懷的參湯。
湯熬好了,一股濃郁的參香在小廚房裡瀰漫開來。布木布泰小心地將參湯倒入一個白瓷碗中,再放入一個有保溫夾層的食盒裡。
她對蘇茉兒說:「你跟我來,記住,從現在開始,多看,多聽,少說話。」
蘇茉兒雖然心中驚疑不定,但還是用力點了點頭,提起了食盒。
主僕二人借著夜色的掩護,悄無聲息地離開了永登宮。深夜的皇城,寒風刺骨,吹得道旁的燈籠搖曳不定,在地上投下鬼魅般的光影。布木布泰緊了緊身上的披風,手心裡緊緊攥著那塊冰冷的令牌,內心卻是一片火熱。
當她來到城北那座戒備森嚴的院落外時,守衛的巴牙喇護軍看到兩個女人深夜到訪,立刻警惕地舉起了手中的兵器。
「來者何人!」
布木布泰沒有說話,只是從袖中取出了那塊刻著滿文的黃銅令牌。為首的護軍頭領借著燈籠的光一看,那令牌上的紋飾和刻字,讓他瞬間倒吸一口涼氣,雙腿一軟,差點跪了下去。這是皇太極從不離身的信物,見此牌如見皇上親臨!
「開……開門!」他結結巴巴地命令道,同時用眼神示意手下人全部退到一邊,不許多看,不許多問。
沉重的木門在「吱呀」聲中被打開,一股混合著霉味、草料味甚至還有一絲若有若無的死亡氣息,從院內撲面而來,讓蘇茉兒忍不住用袖子掩住了口鼻。布木布泰卻像是沒有聞到一樣,面色平靜地邁步走了進去。
在護軍的引領下,她來到那間關押著洪承疇的屋子前。一盞昏黃的油燈掛在門外,映照著那扇緊閉的房門,像一隻窺探地獄的眼睛。
「打開。」布木布泰輕聲說。
鎖鏈被嘩啦啦地取下,門被推開。裡面的景象,比想像中還要糟糕。房間狹小而陰暗,空氣污濁不堪。唯一的家具,就是一張歪歪扭扭的破桌子和幾個草墩。
而房間的角落裡,草堆之上,蜷縮著一團黑乎乎的人影,像一截被遺忘的枯木,一動不動,不知是死是活。
布木布泰讓蘇茉兒留在門口,自己提著裙擺,獨自走了進去。
她沒有像之前的那些人一樣,急著走到洪承疇面前開口說話。她的第一舉動,出乎了所有人的預料。
她先是環顧了一下這個令人窒息的小屋,然後走到那扇僅有的、糊著厚厚窗紙的小窗前。她伸出自己那雙保養得宜的纖纖玉手,用衣袖,輕輕地、仔細地,擦拭著窗紙上積滿的灰塵與污垢。隨著她的動作,一層層的塵埃被拭去,窗紙變得透亮了一些。恰好此時,一片雲彩飄過,一縷清冷的月光,透過那片被擦拭乾凈的窗紙,悄然無聲地照了進來,在地上投下了一小塊銀白色的光斑。
這一個小小的舉動,仿佛給這個密不透風的死亡空間,帶來了一絲微弱的生機。
接著,布木布泰走到那張破桌前,讓蘇茉兒將食盒放了上去。她打開食盒,將那碗還冒著絲絲熱氣的參湯端了出來。濃郁而溫暖的參香味,立刻在這片污濁的空氣中擴散開來,霸道地驅散了部分霉味。
她做完這一切,依舊沒有開口。她端著那碗湯,沒有直接送到洪承疇面前,只是走到了離他三四步遠的地方,將湯碗輕輕地放在了地上。然後,她就在旁邊一個還算乾淨的草墩上,靜靜地坐了下來,雙手交疊放在膝上,一言不發。
時間,在這一刻仿佛凝固了。
牢房裡,只聽得見外面護軍們偶爾走動的腳步聲,風吹過屋檐的嗚咽聲,以及……布木布泰和角落裡那個人影之間,兩種截然不同的呼吸聲。一個平穩而悠長,一個微弱而斷續。
洪承疇依然背對著她,像一座沒有生命的雕塑。但如果有人能靠近看,會發現他那蜷縮的身體,似乎比剛才更加僵硬了。他能感覺到背後有人,能聞到那久違的、帶著暖意的食物香氣。但他想不通,來的是誰?為什麼不說話?
一個尊貴的、帶著侍女、能命令皇上親兵的女人,深夜來到這必死之地,不威逼,不勸誘,只是擦了扇窗,放下一碗湯,然後就這麼靜靜地坐著。
這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難以言喻的心理壓迫,更勾起了他心中一絲幾乎已經泯滅的好奇。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久到蘇茉兒都覺得自己的腿有些發麻了。她焦急地看著自家主子,不明白她葫蘆里到底賣的什麼藥。
就在這令人窒息的沉默中,布木布泰終於開口了。
她的聲音很輕,很柔,像是怕驚擾了這屋裡某個沉睡的精靈,又像是怕這聲音太過突兀,會刺痛一個久處黑暗之人的耳朵。
她沒有說「洪將軍」,更沒有說「皇上讓我來的」。她只是望著地上那碗漸漸失去熱氣的參湯,仿佛在自言自語,又仿佛在對一個許久未見的老朋友閒話家常:
「天,真冷啊。我從一些從關內來的商人那裡聽說,你們南方的冬天,是不下雪的吧?尤其……是福建泉州那邊。想來,那裡的冬天應該也是濕冷的,就像這碗參湯,若是再放一會兒,等到它徹底涼透了,怕是就再也暖不了人的心了。」
這句話,如同一顆投入死水潭的小石子,無聲無息,卻激起了一圈圈深入底部的漣漪。
「福建泉州」——這四個字,像一把失傳已久的鑰匙,在洪承疇那早已被恥辱和絕望銹死的腦海深處,「咔嗒」一聲,精準地插入了那把塵封的心鎖。
他的身體,幾不可察地猛地一顫。這是這麼多天以來,他第一次對外界的刺激,做出如此清晰的反應。
但他依然沒有回頭,也沒有說話。黑暗中,沒人能看清他此刻的表情。
布木布泰也沒有繼續說下去。她再次陷入了沉默,似乎在耐心等待著那把鑰匙,慢慢地轉動。牢房裡的氣氛,比剛才更加詭異和緊張。她像一個最高明的漁夫,已經撒下了網,現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魚兒自己掙扎著入網。
地上的那碗參湯,最後一絲熱氣也散盡了。蘇茉兒看著自家主子,眼中寫滿了焦急,她用眼神催促著,仿佛在說:娘娘,快說點什麼吧!時間不多了!
就在蘇茉兒都以為這次不同尋常的嘗試,終究也要和其他人一樣以失敗告終時,那個蜷縮在草堆里的身影,終於,動了。
他沒有回頭。
他只是用一種極其嘶啞、微弱,如同兩片砂紙在互相摩擦的聲音,從喉嚨的深處,擠出了一個讓布木布泰都感到萬分意外的問題。
他問的不是「你是誰」,也不是「你來做什麼」,更不是讓她「滾開」。
而是——
「你……見過樑上的那隻燕子嗎?它今天……有沒有回來?」
話音剛落,本章結束。這句莫名其妙的話,像一道謎題,橫亘在死寂的牢房之中。他究竟是因飢餓而神志不清,說起了胡話?還是在用一種無人能懂的暗語,進行著最後的試探?這隻神秘的「燕子」,到底是什麼?這個巨大的、匪夷所思的懸念,將牢牢地抓住每一個人的心,迫使他們瘋狂地想要知道,布木布泰將如何應對這個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開局。
06
蘇茉兒聽到這個問題,整個人都懵了。燕子?這冰天雪地的隆冬時節,哪裡來的燕子?她下意識地抬起頭,看了看光禿禿的、結著蛛網的房梁,心裡只有一個念頭:這洪承疇,果然是餓得發了瘋,開始說胡話了。她緊張地看向布木布泰,不知主子該如何接下這句瘋話。
然而,布木布泰的臉上卻毫無意外之色。當聽到「燕子」兩個字時,她的心反而徹底定了下來。她的嘴角,甚至在無人察覺的黑暗中,勾起了一抹瞭然的微笑。
賭對了。
她來之前做的那些看似無用的功課,在這一刻,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她曾通過那個小太監,搜集了所有能找到的,關於洪承疇的軼事。其中有一條就記載著:洪承疇在總督薊遼軍務時,官署大堂的房樑上有一窩燕子。
有一次,燕子受了驚,他為此大發雷霆,甚至責罰了手下的吏員。此事後來被當成一樁趣聞,用以證明他這位鐵血將帥,也有著「愛惜生靈」的仁慈一面。
所以布木布泰瞬間就明白了,洪承疇此刻問的,根本不是什麼真正的燕子。這隻「燕子」,是他內心世界裡一個極其微弱、卻又無比重要的象徵。它象徵著他對「生」的一絲留戀,象徵著他作為一個讀書人心中那點尚未泯滅的「善」與「仁」,象徵著他即便身處絕境,也還在意著那些微小而美好的事物。
他不是在說胡話。他是在用一種極為隱晦、也極為驕傲的方式進行試探。他在問:你,懂我嗎?你究竟是又一個把我當成獵物和工具的說客,還是一個能看透我這身硬殼,看到我內心深處那點柔軟的知己?
這個問題,是最後一道防線,也是唯一的門徑。答對了,門便開了;答錯了,門將永遠關閉。
布木布泰沒有直接回答「有」或者「沒有」。她緩緩站起身,走到那碗已經冰涼的參湯前,彎腰將其端了起來。這個動作,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洪承疇的注意力,儘管他沒有回頭,但他的耳朵一定在聽著。
她走到門口,將那碗涼透了的湯遞給蘇茉兒,輕聲吩咐道:「去,再為將軍熱一碗來。」
做完這一切,她才重新走回草墩邊坐下,目光仿佛穿透了牆壁,望向了外面漆黑的夜空。她用一種帶著些許悵惘和憐惜的語氣,悠悠地說道:
「將軍,外面的風太大了,天也太冷了。樑上的燕子是聰明的鳥兒,它早就帶著一家老小,飛到南方溫暖的地方去過冬了。」
她的聲音頓了頓,仿佛給了洪承疇一個喘息和思考的空間,然後才繼續說下去,聲音裡帶著一層溫柔的喻意:
「它若還傻傻地留在這裡,不肯離去,那結果只有一個,就是和您一樣,在這絕望的寒冬里,活活地凍死、餓死。有時候……暫時的離開,並不是背叛,而是為了等到下一個春天,能夠更好地歸來,重新銜泥築巢啊。」
一番話,舉重若輕。她既無比精準地回答了他的問題,又巧妙地將「燕子」的意象,與他洪承疇自身的處境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她沒有勸他「投降」,而是在告訴他「求生」。她將「投降」這個恥辱的字眼,偷換成了「暫時的離開」和「等待春天」,這其中不帶任何強迫,卻充滿了哲理和人情味。
角落裡,那具僵硬的身體再次劇烈地一震。這一次的震動,比上一次更為明顯。
黑暗中,傳來一陣悉悉索索的響聲。洪承疇,那個幾十天來始終背對眾人,如同石化了一般的男人,竟然緩緩地,用一種極其艱難、仿佛每動一下骨頭都在呻吟的動作,轉過了他的頭。
他第一次,正眼看向了這個深夜來訪的女人。
油燈的光芒從門口斜射進來,只能照亮布木布泰的側臉。他看不清她的全貌,只能看到一個年輕的、柔和的輪廓,和一雙在昏暗中依舊閃爍著智慧與真誠光芒的眼睛。那雙眼睛裡,沒有貪婪,沒有算計,沒有逼迫,只有平靜的關切和深深的理解。
這個女人,懂他。
這個念頭,像一道閃電,劈開了洪承疇心中混沌的黑暗。幾十天了,這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懂他的人。
布木布泰沒有被他那張形同鬼魅的臉嚇到。她迎著他審視的目光,微微頷首,算是打了招呼。然後,她便不再看他,而是自顧自地,聊起了一些看似完全無關緊要的事情。
「聽那些商人說,將軍的家鄉泉州,是個頂好頂好的地方。那裡有個叫刺桐港的,幾百年前就是天底下最熱鬧的港口,世界各地的船都往那裡跑。」
「他們還說,泉州人最愛喝一種茶,叫功夫茶。用很小的茶杯,喝起來特別講究,能品出人生的千百種滋味。想來,那茶的味道,一定能解鄉愁吧。」
她就像一個普通的鄰家女子,在與人閒話家常。她說的每一句話,都像一片溫暖的羽毛,輕輕地,拂過洪承疇心中最柔軟、最敏感的地方。家鄉、港口、功夫茶……
這些遙遠而親切的意象,喚醒了他被囚禁已久的記憶,讓他暫時忘記了自己是個階下囚,而重新記起,他還是那個來自福建南安的讀書人。
更讓他感到震驚的是,布木布泰竟然聊起了他年輕時寫的一首詩。
「臣妾偶然間讀到將軍早年所作的一首七律,其中一句『仗劍還須學冠軍,磨盾終見枕戈人』,真是豪情萬丈。可後面那句『故園楊柳依依在,何日東風送我還』,又充滿了文人的細膩與感傷。臣妾當時就在想,能寫出這樣詩句的人,一定是個心中既有金戈鐵馬,又有綠柳江南的奇男子。」
洪承疇的眼眶,猛地一熱。那幾乎已經乾涸的淚腺,竟然有了一絲濕意。
他的詩!連他自己都快要忘記的少年之作,竟然被一個身在盛京深宮裡的異族女子,記得如此清楚,還品讀得如此透徹!
他那顆早已沉入死水的心,開始不由自主地跳動起來。這幾十天,所有人都把他當成一扇需要撞開的門,只有眼前這個女人,把他當成一本需要細細品讀的書。
這種被理解、被尊重、被當成「知己」的感覺,是他在這冰冷的清營里,從未體會過的溫暖。他那道堅不可摧的心理防線,在金錢、地位、酷刑、親情牌面前都毫髮無損,此刻,卻在這看似無力的溫言軟語之中,悄然出現了一道真正的、深刻的裂縫。
就在這時,蘇茉兒端著第二碗熱氣騰騰的參湯走了進來。這一次,她將湯碗直接放在了洪承疇的面前。
洪承疇的喉結,不受控制地上下滾動了一下。
他終於開口了。聲音依然沙啞得厲害,但不再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冰冷,而是帶著一絲遲疑和探究。
「你……究竟是誰?」
07
牢房裡的氣氛,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當洪承疇問出「你是誰」這個問題時,就代表著他已經從一個完全封閉的自我世界裡,探出了一個頭。他開始對外界產生好奇,開始願意進行一場真正的對話。
布木布泰知道,攻心之戰,已經取得了第一階段的勝利。現在,是時候進入最核心、最關鍵的環節了。
她沒有直接回答自己的身份,因為「莊妃」這個名號,只會重新將他們拉回君臣、敵我的對立面。她只是平靜地看著他的眼睛,用一種更加嚴肅和懇切的語氣說道:
「我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一個敬佩將軍忠義的人。」
她先是毫不吝嗇地給予了對方最高的肯定和尊重。「將軍被俘至今,一心求死,為的是全大明之忠,報崇禎皇帝知遇之恩。這份風骨,這份氣節,天下誰人能不敬佩?我雖是一介女流,也發自內心地敬佩您。」
這番話,讓洪承疇緊繃的神經稍稍放鬆了一些。對方沒有像其他人一樣,一上來就否定他的價值觀,指責他「不識時務」,這讓他感覺到了被尊重。
然而,布木布泰的話鋒,緊接著便是一個凌厲無比的轉折。她拋出了一個他從未思考過,也足以顛覆他整個信仰體系的顛覆性問題:
「可是,將軍,您有沒有想過。您的這份『忠』,究竟是忠於那個氣數將盡、風雨飄搖的朱家王朝,還是……忠於這天底下千千萬萬,正在戰火中苦苦掙扎的黎民百姓?」
這句話,如同一道驚雷,在洪承च्यू那虛弱卻依舊高傲的腦海中轟然炸響!
忠於百姓?
他愣住了,嘴唇微微張開,卻發不出任何聲音。這個概念,對他這個浸淫儒家經典數十年的傳統士大夫來說,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古訓,陌生的是,他從未想過,有一天「忠君」和「忠民」會成為一道需要他做出抉擇的題目。
布木布泰沒有給他太多震驚的時間,她乘勝追擊,將這個論點層層深入地剖析開來,聲音不高,卻字字句句都像重錘,敲打在洪承疇的心坎上。
「將軍請看今日之天下!關內,流寇四起,李自成、張獻忠之流,所過之處,赤地千里,百姓流離失所,易子而食,其狀之慘,不忍卒睹!關外,我大清兵鋒正盛,入主中原已是早晚之事。大明江山,實際上早已是千瘡百孔,分崩離析。」
「在這種情勢下,將軍您若一死了之,確實,您成全了您個人的千秋名節,史書上會記下『洪承疇兵敗殉國』這幾個字。可是,然後呢?」
她身體微微前傾,目光灼灼地盯著他:「然後,您這一身匡時濟世的驚天緯地之才,您這滿腹可以安邦定國的良謀大策,難道就要隨著您這副枯骨,一同被埋入這北地的黃土之下嗎?!」
「將軍想一想,當初崇禎皇帝提拔您,重用您,將大明最精銳的部隊交給您,他所期望的,難道僅僅是您為他朱家一人一姓去死嗎?不!他期望的,是您能用您的才華和能力,為他掃平流寇,抵禦外敵,還天下一個太平,讓黎民百姓能夠安居樂業!」
「如今,雖然君主可能要換了,但這天下,還是那個天下;這天下的百姓,還是那些無辜的百姓!一個真正的忠臣,他的『小忠』,是忠於某一個君主;而他的『大忠』,最終應該是忠於天下蒼生,忠於這片土地上所有的生靈啊!」
洪承疇的呼吸變得急促起來。布木布泰的話,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精準地切開了他用「忠君」理念構築的堅固堡壘,讓他看到了一個更宏大,也更具責任感的圖景。
他想起了自己從北京一路領兵至松山的沿途所見。那些面黃肌瘦的災民,那些倒在路邊的餓殍,那些因為戰亂而破碎的家庭,一幕一幕,重新在他眼前浮現。他當初手握重兵,最大的願望,不正是要結束這一切嗎?
布木布泰的聲音變得更加柔和,也更加具有穿透力。
「求死,是一件容易的事。眼睛一閉,牙一咬,所有痛苦、所有掙扎、所有罵名,就都與您無關了。那是解脫。」
「可是,求生,並且是背負著『變節』『投降』的千古罵名去求生,去利用敵人的力量,去完成自己未竟的抱負,去親手結束這場讓億萬生靈塗炭的戰亂……那才是更需要巨大勇氣和擔當的艱難選擇啊!」
「將軍,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留得您這有用之身,將來無論是輔佐新君,制定善待漢人的策略,還是獻計獻策,早日平定天下,讓百姓們能少流一些血,早一天吃上一口飽飯。這……難道不是一種更高層次,也更具意義的『盡忠』嗎?」
一番話,擲地有聲,振聾發聵。
布木布泰沒有試圖去撲滅洪承疇心中的「忠義之火」,恰恰相反,她用一種全新的方式,為這團火焰找到了一個更宏大、更光明的燃燒方向。她沒有否定他的過去,而是為他的未來,提供了一個可以被他自己內心所接受的,全新的道德台階。
洪承疇的世界觀,在這一刻,發生了劇烈的動搖,甚至可以說是崩塌與重建。他一直以來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信條所禁錮,將個人的氣節看得比什麼都重。但布木布泰卻為他打開了另一扇窗戶,窗外,是他曾經發誓要拯救的,水深火熱中的天下蒼生。
是選擇成就個人的「忠烈」之名,然後任由天下繼續糜爛?還是選擇背負萬世的罵名,卻能有機會親手去實現「兼濟天下」的政治抱負?
這個選擇題,太過艱難,也太過沉重。他的內心,掀起了滔天海嘯。堅守了半生的信仰,與一個更加宏大的人道主義理想,在他的腦海中激烈地交戰著。他那張乾枯的臉上,肌肉不住地抽搐,眼神中充滿了痛苦、迷茫和劇烈的掙扎。
08
看著洪承疇眼中那片翻江倒海的掙扎,布木布泰知道,他那堅固的信仰堤壩已經出現了無數裂痕,距離徹底決堤,只差最後一股推力。
她沒有再用那些宏大的道理去衝擊他,而是從袖中,緩緩地取出了一件東西——一面製作精巧的,可以隨身攜帶的銅柄小鏡子。這是後宮女子常用的物件,此刻卻成了她最後的,也是最厲害的武器。
她將鏡子遞到洪承疇的面前,鏡面正對著他的臉。她的聲音,也從剛才的慷慨激昂,轉為一種帶著無限憐憫的輕柔。
「將軍,您看看您自己。您看看鏡子裡的這個人。」
洪承疇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那片小小的、光亮的鏡面上。
鏡子裡,是一張怎樣可怕的臉啊!頭髮像一叢枯草,鬍子拉碴,糾結成團。眼窩深陷,如同兩個黑洞。嘴唇乾裂,布滿了血口。整張臉頰沒有一絲血色,只剩下一層蠟黃的、緊緊包裹著骨頭的皮膚。這哪裡還是當初那個意氣風發、統領十三萬大軍的薊遼總督?這分明就是一個從地獄裡爬出來的,形容枯槁、不成人形的餓鬼。
他自己的模樣,讓他自己都感到一陣心驚。
布木布泰的聲音,適時地在他耳邊響起,像一聲溫柔的嘆息:
「將軍,您一心求死,可您想過沒有,您遠在福建南安家中的那位老母親……她若是看到您如今這副模樣,是會為您所謂的『盡忠殉國』而感到欣慰,還是會為白髮人送黑髮人而肝腸寸斷、哭瞎了雙眼?」
「老母親」這三個字,如同一柄最沉重的巨錘,毫無花哨地,狠狠地砸在了洪承疇內心最柔軟、最脆弱的地方。
「聖人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布木布泰的聲音,仿佛帶著一種魔力,每一個字都清晰地鑽進他的心裡,「您為了君主盡了愚忠,卻要陷自己的母親於不孝、不慈的萬劫不復之地。讓她在晚年,不僅要承受喪子之痛,還要承受因您『叛國』被俘而可能帶來的種種牽連……將軍,這,真的是您想要的『全節』嗎?」
「忠」與「孝」,自古以來就是懸在所有中國讀書人頭上的兩座大山。當它們不衝突時,便是完美的道德楷模;當它們發生劇烈衝突時,足以讓任何一個鐵漢崩潰。
在此之前,洪承疇認為「忠」大於「孝」,為國盡忠,便是最大的孝。但布木布泰卻為他展示了另一面:你死了,你的「忠」結束了,可你留給母親的「不孝」之痛,卻是永無止境的。你的死,是一種自私的成全,卻是對母親最殘忍的拋棄。
對君主的忠誠,在這一刻,與對母親最本原的牽掛和愧疚,與對天下蒼生的責任感,這三股力量交織在一起,終於壓垮了他心中那根名為「愚忠」的最後的稻草。
他緩緩地抬起頭,目光從那面讓他自己都感到陌生的鏡子上移開,落在了面前那碗早已不再滾燙,卻依舊散發著溫暖氣息的參湯上。
他看著湯,又看看眼前這位比自己小了將近二十歲,看似柔弱,卻有著驚人智慧和深刻洞察力的年輕女子。她不是來勸降的魔鬼,她分明是來點醒他,渡他出這無間地獄的菩薩。
長久的,死一般的沉默。
牢房裡,只聽得到洪承疇那愈發粗重的呼吸聲。
終於,他那隻如同枯枝般的手,顫抖著,緩緩地伸了出來,伸向了那隻白瓷碗。他的動作很慢,很艱難,仿佛用盡了畢生的力氣。
他端起了那碗湯。
然後,在布木布泰平靜的注視下,他仰起頭,將那碗凝聚了希望、理由和新生的參湯,一飲而盡。
這是他被俘數十日以來,第一次主動進食。
湯水入喉,仿佛一股暖流,瞬間流遍了他那幾近乾涸的四肢百骸。身體上的暖意,點燃了心理上的生機。
他放下空碗,那雙已經有了些許神采的眼睛,深深地看著布木布泰。然後,他掙扎著,挪動著自己僵硬的身體,對著眼前這個女子,緩緩地,鄭重地,跪了下去。
這個跪,不是對一個妃子的跪拜,而是一個迷途之人,對指引他方向的「知己」的感謝。
他沙啞地開口,說出了那句徹底改變了他自己,也深刻影響了未來歷史走向的話:
「罪臣……洪承疇……但求速見大清皇帝。另……另請……為我剃髮。」
剃髮易服,這是投降歸順最徹底、最無可辯駁的象徵。從說出這句話的這一刻起,大明的薊遼總督洪承疇,已經死了。活下來的,將是大清的臣子,洪承疇。
天色微明,當第一縷晨曦刺破盛京上空的黑暗時,布木布泰裹緊披風,平靜地走出了那座院落。她的臉上看不出喜悅,也看不出疲憊,只有一種如深潭般的沉靜。
不久之後,整個大清朝堂都為之震動。
那個寧死不屈、水米不進的硬骨頭洪承疇,在沐浴更衣之後,剃去了他珍視的髮髻,換上了滿洲官員的服飾,精神抖擻地出現在了皇太極的面前,叩首稱臣。
滿朝文武,尤其是那些輪番上陣卻屢屢碰壁的漢臣和滿洲親貴,一個個都目瞪口呆,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們絞盡了腦汁,也想不明白,就在那個所有人都以為洪承疇必死無疑的夜晚,那個年輕美貌的莊妃,在那個陰暗的密室里,在那短短的幾個小時之內,究竟對他施了什麼樣的魔法?
大政殿之上,皇太極在接受了洪承疇的跪拜,並授予他高官厚祿之後,目光越過歡欣鼓舞的群臣,望向了遠遠站在後宮嬪妃人群之中的布木布泰。她依舊是那副恬靜淡然、與世無爭的模樣,仿佛昨夜那場驚心動魄的博弈與她毫無關係。
但皇太極的心中卻雪亮。他知道,從今夜起,他不僅得到了一個能為他打開中原大門的洪承疇,更重要的是,他重新認識了自己身邊這位來自科爾沁草原的妃子。她擁有的,不僅僅是美貌,更是一種足以影響國運的、深不可測的政治智慧。
數日後,已經恢復了昔日幾分神采的洪承疇,身著嶄新的大清官服,獨自一人登上了盛京的城樓。
他憑欄遠眺,望著南方那片他曾經浴血守護,如今卻已成故國的土地,眼神複雜無比。寒風吹動著他額前那根金錢鼠尾辮,也吹起了他心中的萬千思緒。
他知道,從今往後,他將永遠地背負「漢奸」「叛徒」的千古罵名。但他心中,也燃起了一團全新的火焰。那是在那個寒冷的夜晚,由一個女人為他親手點燃的——那是「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更宏大的責任之火。
沒有人用刀劍逼迫他,沒有人用金銀誘惑他。
孝莊,那個年僅二十餘歲的女子,她只是用一個女人的細膩,和一種超越常人的智慧,看穿了一個男人的驕傲,讀懂了一個文人的掙扎,解構了一個忠臣的信仰。
然後,她又親手為他重塑了一個可以讓他自己說服自己,並昂首活下去的理由。她讓他深刻地明白:有時候,苟且地活著,比壯烈地死去,需要更大的勇氣,也蘊含著更深遠的價值。
這,就是那數小時密談中,真正的不傳之秘。
 呂純弘 • 133K次觀看
呂純弘 • 133K次觀看 呂純弘 • 12K次觀看
呂純弘 • 12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花峰婉 • 17K次觀看
花峰婉 • 17K次觀看 呂純弘 • 10K次觀看
呂純弘 • 10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9K次觀看
呂純弘 • 9K次觀看 奚芝厚 • 9K次觀看
奚芝厚 • 9K次觀看 呂純弘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滿素荷 • 4K次觀看
滿素荷 • 4K次觀看 喬峰傳 • 34K次觀看
喬峰傳 • 34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24K次觀看
呂純弘 • 2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9K次觀看
呂純弘 • 49K次觀看 幸山輪 • 22K次觀看
幸山輪 • 22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