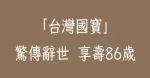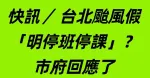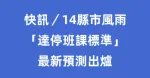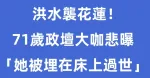1/3
下一頁
清軍無人能勸降洪承疇,20歲孝莊只身前往,說了什麼讓他剃髮易服

1/3
清軍無人能勸降洪承疇,20歲孝莊只身前往,說了什麼讓他剃髮易服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本文所用素材源於網際網路,部分圖片非真實圖像,僅用於敘事呈現,請知悉
「他還是不肯?」皇太極的聲音在大殿里迴響,帶著一絲罕見的疲憊。
范文程跪在地上,頭埋得更低了:「回皇上,洪承疇心意已決,水米不進,只求速死。」
「廢物!」皇太極一掌拍在龍椅扶手上,「滿朝文武,竟奈何不了一個將死之人!」
殿角,一位年輕的妃子將剝好的橘瓣放入兒子口中。
聽到這話,她抬起頭,輕聲對身邊的侍女說:「你看,所有人都想讓他『降』,可一個一心求死的人,你怎麼能勸他『生』?」
01
盛京的初冬,寒氣已經能鑽進骨頭縫裡。城北一座不起眼的院落,外面看是青磚灰瓦的普通民居,內里卻三步一哨、五步一崗,守衛的都是黃太極麾下最精銳的正黃旗巴牙喇(護軍)。這裡,與其說是一座宅院,不如說是一座為一個人量身定做的黃金囚籠。
囚籠的主人,是前明薊遼總督、在松山血戰中兵敗被俘的洪承疇。
范文程緊了緊身上的貂裘,從那間死氣沉沉的屋子裡走了出來,臉上掛著深深的疲憊和挫敗。寒風迎面吹來,他忍不住打了個哆嗦,這冷意,一半來自天氣,一半來自屋裡那個男人如頑石般的意志。院子裡,一箱箱打開的木箱在慘白的冬日陽光下閃著刺眼的光。箱子裡,黃澄澄的金元寶、光華流轉的東珠、觸手生溫的和田玉,還有一匹匹江南織造局出品的頂級絲綢,這些能讓世上九成九的人瘋狂的東西,如今卻像一堆無人問津的垃圾,靜靜地躺在那裡,蒙上了一層薄薄的灰。
屋裡,洪承疇背對著門口,一動不動。他身上還穿著那件早已髒污不堪、邊角都起了毛的明朝緋色官袍,這身衣服是他最後的尊嚴。他已經在這兒被「禮遇」了數十天,身形早已脫相,原本還算豐滿的臉頰深深地凹陷下去,只剩下一副高聳的顴骨和幾乎要刺破皮膚的胡茬。他整個人,像一尊面朝南方、正在風化的石像,對身後的所有喧囂與誘惑都置若罔聞。
他已經絕食數日了。
起初,清廷送來的是山珍海味,由專門的廚子烹飪,意在顯示其優待。洪承疇看也不看。後來,送飯的換成了與他有過幾面之緣的降將,想打打感情牌。
洪承疇用盡全身力氣,將那精緻的食盒連同裡面的飯菜一併掃落在地,然後重新縮回牆角,閉上眼睛,仿佛剛才耗盡了他所有的生命力。
他的目光總是空洞地望著那面南牆,仿佛穿透了厚厚的牆壁,看到了山海關,看到了北京城,看到了金鑾殿上那個對他寄予厚望的崇禎皇帝。
他的心裡像有一鍋燒開的沸水,翻騰著的全是悔恨與羞恥。悔恨自己為何沒能戰死在松山城頭,卻成了這階下之囚;羞恥自己身為大明經略,受皇恩浩蕩,如今卻要被一群「建州女真」的韃子當作戰利品一樣觀賞、勸誘。
在他看來,一個文人,一個讀聖賢書、受皇上知遇之恩的封疆大吏,兵敗的唯一結局就是以身殉國,殺身成仁。投降?這兩個字,比拿刀子在他心口上剜肉還要讓他痛苦萬分。
「還是老樣子?」一個聲音在范文程身邊響起。
范文程回頭,是另一位漢臣寧完我,他的臉上同樣布滿了愁雲。「還能有什麼新樣子?」范文程苦笑著搖了搖頭,指了指屋裡,「水米不進,油鹽不入。皇上賞的這些東西,他連碰都懶得碰一下。再這麼下去,不出三五天,人就沒了。咱們這位洪亨九(洪承疇的字),是鐵了心要去見崇禎皇帝了。」
寧完我嘆了口氣:「這人就是個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可皇上偏偏就看重他,說他是打開關內局面的鑰匙。現在倒好,鑰匙快要自己斷了。」
他們這些漢臣,心裡其實五味雜陳。一方面,他們是真心為新主子皇太極效力,渴望建功立業;另一方面,面對洪承疇這種寧死不屈的「忠」,他們內心深處又有一絲難以言說的敬佩和一絲作為同類的尷尬。每一次勸降的失敗,都像是一記耳光,打在他們這些「識時務者」的臉上。
這個消息很快傳回了清宮。
大政殿里,地龍燒得暖烘烘的,可皇太極的心裡卻像是結了冰。他高大的身軀在鋪著黃毯的地上煩躁地來回踱步,松錦大捷的喜悅,早被這個不肯低頭的囚犯消磨得一乾二淨。
「廢物!通通都是廢物!」他猛地停下腳步,對著面前一眾束手而立的王公大臣和漢臣們咆哮,「幾十天了!一個活人,還不如一座死城難打!你們這些漢人,不是最懂漢人嗎?怎麼到了他洪承疇面前,一個個都成了鋸嘴的葫蘆?」
以多爾袞為首的幾位滿洲親貴面露不屑。一個粗豪的武將忍不住站了出來,瓮聲瓮氣地說道:「皇上,依臣看,就是咱們對這些漢人讀書官太客氣了!把他扔進大牢,大刑伺候一遍,鞭子、烙鐵輪番上,不怕他不把知道的都吐出來!」
「糊塗!」皇太極一拍桌子,震得茶碗都跳了一下,「朕要的是他心甘情願地歸順,為我大清開疆拓土!朕要的是他的腦子,他的人望,是他這杆明朝文武官員心中的大旗!朕要讓他成為我大清吸納漢人的一塊磁石,不是要一具被嚇破了膽的行屍走肉!用刑?那跟殺了他有什麼區別?朕若只要他死,何必費這麼大功夫!」
皇太極的怒吼在大殿里迴蕩,眾人噤若寒蟬。范文程硬著頭皮上前一步,躬身道:「皇上息怒。洪承疇此人,是塊滾刀肉,更是個死心眼兒。他將個人名節看得比天還大。尋常法子,怕是……真的沒用。咱們用金銀美女去誘他,在他看來,是對他最大的侮辱。」
范文程頓了頓,似乎想起了什麼,又補充道:「不過……臣倒聽看守的人說起一樁怪事。洪承疇雖水米不進,但昨夜裡,他似乎一直在低聲念叨著什麼,聲音很輕,像是囈語。看守隔著門縫聽了半天,像是在叫一個人的名字,又像是在背一首他年輕時候寫的詩……」
這個細節,像一根針,輕輕刺了皇太極一下。他焦躁的眼神瞬間銳利起來,追問道:「念叨什麼?叫誰的名字?」
范文程卻搖了搖頭,滿臉的遺憾:「夜深人靜,離得又遠,那看守沒聽真切。只覺得他不像前幾日那般完全死寂了,心裡頭……似乎還有點挂念的東西。」
皇太極眉頭緊鎖,這個沒頭沒尾的線索,非但沒能幫他,反而更添了一絲煩亂。
一個一心求死的人,心裡還有挂念?那會是什麼?是他在明朝的妻兒老小?還是別的什麼不為人知的秘密?這絲挂念,是能撬開他嘴巴的縫隙,還是他臨死前的最後一點執念?
無人能給出答案。
盛京城裡的勸降努力,就這樣陷入了僵局。而洪承疇的生命,也如沙漏中的細沙,一點一滴地流向盡頭。
幾天後,宮中設宴,算是為前線的將士們慶功。酒過三巡,菜過五味,皇太極的興致卻始終不高。他端著酒杯,看著殿下歌舞昇平的熱鬧景象,心裡想的還是那個冰冷的囚籠和那個倔強的靈魂。
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帶著幾分酒意,對著滿座的後宮嬪妃和皇子們抱怨道:「松錦一戰,朕俘獲虎將無數,獨獨這個洪承疇,軟硬不吃,真是讓朕寢食難安。滿朝文武,竟無一人能為朕解此憂愁!」
這話一出,殿內的絲竹聲都仿佛弱了下去。嬪妃們個個低眉順眼,大氣不敢出。這種軍國大事,她們哪裡敢插嘴,說對了沒賞,說錯了可能就是一場災禍。
一片寂靜中,只有在筵席的角落裡,一位年僅二十餘歲的年輕妃子——來自科爾沁草原的博爾濟吉特·布木布泰,也就是被封為西宮永福宮側福晉的莊妃,似乎並未受到這壓抑氣氛的影響。
她正低著頭,用她那雙纖細白皙的手,耐心地為身邊年幼的兒子福臨剝著一個金黃的橘子。她的動作很輕柔,很專注,仿佛整個世界的紛擾都與她無關,眼中只有她心愛的兒子和手中的橘子。
可當皇太極那句充滿無奈的抱怨飄進她耳朵里時,她剝橘子的手,幾不可察地微微頓了一下。一片橘絡被她輕輕撕下,她抬起頭,那雙清澈如草原上湖泊的眼眸,越過人群,望向主位上那個愁眉不展的男人。
她的眼神里,沒有旁人的畏懼與惶恐,反而流露出一絲極深的思索,一種仿佛獵人看到獵物時才有的專注與探究。
02
莊妃布木布泰的永福宮,在整個盛京後宮裡,算是一個特別的存在。這裡不像關雎宮宸妃海蘭珠那裡,時常能聽到皇太極爽朗的笑聲;也不像麟趾宮貴妃娜木鐘那裡,總是聚集著一群蒙古來的親貴妃嬪,熱鬧非凡。永福宮總是很安靜,安靜得像它主人的性子一樣,內斂而深沉。
布木布泰並沒有像大多數後宮女子那樣,將自己的一生寄托在爭風吃醋和等待君王的垂青上。對她而言,這深宮大院,既是她的家,也是她的戰場,更是她觀察和學習的課堂。
清晨,當別的妃子還在梳妝打扮時,她已經陪著兒子福臨在窗邊讀書了。她教的,並非死記硬背《三字經》《百家姓》。她會指著書上的「馬」字,給福臨講科爾沁草原上萬馬奔騰的壯闊景象;她會講到「忠」字,給兒子講那些草原上為了部落榮耀而戰死的英雄故事。她總能把那些枯燥的方塊字,變得有血有肉,有聲有色。福臨在她身邊,總是聽得入了迷。
午後,她會親自到宮裡的小花圃里,拿起小鋤頭鬆土。
侍女看不過去,想上來幫忙,她總是笑著擺擺手:「不用,讓我自己來。」她一邊翻動著濕潤的泥土,一邊對侍女蘇茉兒說:「你看,這土和人心是一個道理。你得時常給它鬆動鬆動,透透氣,它才不會板結。土一板結,再好的種子也扎不下去根;人心一板結,再好的道理也聽不進去。」蘇茉兒似懂非懂地點點頭,只覺得娘娘說的話,總是那麼有嚼頭。
布木布泰的智慧,更多時候體現在那些細微的人情世故里。有一次,貴妃娜木鐘宮裡的一個太監,仗著主子得勢,故意找茬,說永福宮的宮女走路沒看道,衝撞了他。那小宮女嚇得臉都白了。布木布泰聽聞後,不急不躁地走了出來,臉上帶著溫和的笑意。
她沒有直接去質問那太監,也沒有為自己的宮女辯護,而是先對那太監說:「喲,這不是李公公嗎?瞧您這身子骨,越發硬朗了。昨兒皇上還夸娜木鐘姐姐宮裡的人懂規矩,想來就是您調教有方。我這宮裡的小丫頭笨手笨腳的,回頭我一定好好說說她。您大人有大量,可千萬別跟她一般見識,氣壞了身子可不值當。」
一番話下來,既捧了娜木鐘,又誇了太監,還順帶把自己的宮女摘了出來。那太監本來是來找茬的,被她這麼一戴高帽,再想發作也拉不下臉來,只好訕訕地說了幾句場面話,灰溜溜地走了。
事後,蘇茉兒佩服得五體投地:「娘娘,您可真厲害!三言兩語就把那個惡人打發了。」
布木布泰只是淡淡一笑,理了理衣袖:「在這宮裡,硬碰硬是最蠢的法子。拳頭打在棉花上,才最讓對方難受。記住,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柔能克剛,也是這個道理。」
她就是這樣,用一種遠超她二十幾歲年齡的沉穩和高情商,在暗流洶湧的後宮中,為自己和兒子福臨撐起了一片安穩的天地。但她的眼光,從未只局限於這四方的宮牆之內。
她不像別的妃子那樣,只關心皇上今晚翻了誰的牌子,賞了誰家珠寶。她更關心皇上的眉毛,是舒展著,還是緊鎖著。
她知道,皇太極的喜怒哀樂,直接關係到大清的國運,也直接關係到她和福臨的未來。她對皇太極的感情是複雜的,不僅僅是夫妻之情,更有一種對草原雄鷹的敬佩,以及將自己命運與之牢牢捆綁在一起的依附感。她清楚地知道,她的榮耀,她兒子的前途,都維繫在皇太極的宏圖偉業之上。
所以,當「洪承疇」這個名字,開始頻繁地出現在從前朝傳到後宮的只言詞組中時,她便敏銳地察覺到,這三個字,已經成了壓在皇太太極心頭的一塊巨石。
每當夜深人靜,皇太極帶著一身疲憊來到永福宮時,布木布泰從不主動去問前朝的煩心事。她只是默默地為他換上舒適的便服,親手端上一碗溫熱的奶茶,或者為他輕輕地按揉著太陽穴。在這樣溫柔而寧靜的氛圍里,皇太極反而會忍不住傾訴幾句。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本文所用素材源於網際網路,部分圖片非真實圖像,僅用於敘事呈現,請知悉
「他還是不肯?」皇太極的聲音在大殿里迴響,帶著一絲罕見的疲憊。
范文程跪在地上,頭埋得更低了:「回皇上,洪承疇心意已決,水米不進,只求速死。」
「廢物!」皇太極一掌拍在龍椅扶手上,「滿朝文武,竟奈何不了一個將死之人!」
殿角,一位年輕的妃子將剝好的橘瓣放入兒子口中。
聽到這話,她抬起頭,輕聲對身邊的侍女說:「你看,所有人都想讓他『降』,可一個一心求死的人,你怎麼能勸他『生』?」
01
盛京的初冬,寒氣已經能鑽進骨頭縫裡。城北一座不起眼的院落,外面看是青磚灰瓦的普通民居,內里卻三步一哨、五步一崗,守衛的都是黃太極麾下最精銳的正黃旗巴牙喇(護軍)。這裡,與其說是一座宅院,不如說是一座為一個人量身定做的黃金囚籠。
囚籠的主人,是前明薊遼總督、在松山血戰中兵敗被俘的洪承疇。
范文程緊了緊身上的貂裘,從那間死氣沉沉的屋子裡走了出來,臉上掛著深深的疲憊和挫敗。寒風迎面吹來,他忍不住打了個哆嗦,這冷意,一半來自天氣,一半來自屋裡那個男人如頑石般的意志。院子裡,一箱箱打開的木箱在慘白的冬日陽光下閃著刺眼的光。箱子裡,黃澄澄的金元寶、光華流轉的東珠、觸手生溫的和田玉,還有一匹匹江南織造局出品的頂級絲綢,這些能讓世上九成九的人瘋狂的東西,如今卻像一堆無人問津的垃圾,靜靜地躺在那裡,蒙上了一層薄薄的灰。
屋裡,洪承疇背對著門口,一動不動。他身上還穿著那件早已髒污不堪、邊角都起了毛的明朝緋色官袍,這身衣服是他最後的尊嚴。他已經在這兒被「禮遇」了數十天,身形早已脫相,原本還算豐滿的臉頰深深地凹陷下去,只剩下一副高聳的顴骨和幾乎要刺破皮膚的胡茬。他整個人,像一尊面朝南方、正在風化的石像,對身後的所有喧囂與誘惑都置若罔聞。
他已經絕食數日了。
起初,清廷送來的是山珍海味,由專門的廚子烹飪,意在顯示其優待。洪承疇看也不看。後來,送飯的換成了與他有過幾面之緣的降將,想打打感情牌。
洪承疇用盡全身力氣,將那精緻的食盒連同裡面的飯菜一併掃落在地,然後重新縮回牆角,閉上眼睛,仿佛剛才耗盡了他所有的生命力。
他的目光總是空洞地望著那面南牆,仿佛穿透了厚厚的牆壁,看到了山海關,看到了北京城,看到了金鑾殿上那個對他寄予厚望的崇禎皇帝。
他的心裡像有一鍋燒開的沸水,翻騰著的全是悔恨與羞恥。悔恨自己為何沒能戰死在松山城頭,卻成了這階下之囚;羞恥自己身為大明經略,受皇恩浩蕩,如今卻要被一群「建州女真」的韃子當作戰利品一樣觀賞、勸誘。
在他看來,一個文人,一個讀聖賢書、受皇上知遇之恩的封疆大吏,兵敗的唯一結局就是以身殉國,殺身成仁。投降?這兩個字,比拿刀子在他心口上剜肉還要讓他痛苦萬分。
「還是老樣子?」一個聲音在范文程身邊響起。
范文程回頭,是另一位漢臣寧完我,他的臉上同樣布滿了愁雲。「還能有什麼新樣子?」范文程苦笑著搖了搖頭,指了指屋裡,「水米不進,油鹽不入。皇上賞的這些東西,他連碰都懶得碰一下。再這麼下去,不出三五天,人就沒了。咱們這位洪亨九(洪承疇的字),是鐵了心要去見崇禎皇帝了。」
寧完我嘆了口氣:「這人就是個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可皇上偏偏就看重他,說他是打開關內局面的鑰匙。現在倒好,鑰匙快要自己斷了。」
他們這些漢臣,心裡其實五味雜陳。一方面,他們是真心為新主子皇太極效力,渴望建功立業;另一方面,面對洪承疇這種寧死不屈的「忠」,他們內心深處又有一絲難以言說的敬佩和一絲作為同類的尷尬。每一次勸降的失敗,都像是一記耳光,打在他們這些「識時務者」的臉上。
這個消息很快傳回了清宮。
大政殿里,地龍燒得暖烘烘的,可皇太極的心裡卻像是結了冰。他高大的身軀在鋪著黃毯的地上煩躁地來回踱步,松錦大捷的喜悅,早被這個不肯低頭的囚犯消磨得一乾二淨。
「廢物!通通都是廢物!」他猛地停下腳步,對著面前一眾束手而立的王公大臣和漢臣們咆哮,「幾十天了!一個活人,還不如一座死城難打!你們這些漢人,不是最懂漢人嗎?怎麼到了他洪承疇面前,一個個都成了鋸嘴的葫蘆?」
以多爾袞為首的幾位滿洲親貴面露不屑。一個粗豪的武將忍不住站了出來,瓮聲瓮氣地說道:「皇上,依臣看,就是咱們對這些漢人讀書官太客氣了!把他扔進大牢,大刑伺候一遍,鞭子、烙鐵輪番上,不怕他不把知道的都吐出來!」
「糊塗!」皇太極一拍桌子,震得茶碗都跳了一下,「朕要的是他心甘情願地歸順,為我大清開疆拓土!朕要的是他的腦子,他的人望,是他這杆明朝文武官員心中的大旗!朕要讓他成為我大清吸納漢人的一塊磁石,不是要一具被嚇破了膽的行屍走肉!用刑?那跟殺了他有什麼區別?朕若只要他死,何必費這麼大功夫!」
皇太極的怒吼在大殿里迴蕩,眾人噤若寒蟬。范文程硬著頭皮上前一步,躬身道:「皇上息怒。洪承疇此人,是塊滾刀肉,更是個死心眼兒。他將個人名節看得比天還大。尋常法子,怕是……真的沒用。咱們用金銀美女去誘他,在他看來,是對他最大的侮辱。」
范文程頓了頓,似乎想起了什麼,又補充道:「不過……臣倒聽看守的人說起一樁怪事。洪承疇雖水米不進,但昨夜裡,他似乎一直在低聲念叨著什麼,聲音很輕,像是囈語。看守隔著門縫聽了半天,像是在叫一個人的名字,又像是在背一首他年輕時候寫的詩……」
這個細節,像一根針,輕輕刺了皇太極一下。他焦躁的眼神瞬間銳利起來,追問道:「念叨什麼?叫誰的名字?」
范文程卻搖了搖頭,滿臉的遺憾:「夜深人靜,離得又遠,那看守沒聽真切。只覺得他不像前幾日那般完全死寂了,心裡頭……似乎還有點挂念的東西。」
皇太極眉頭緊鎖,這個沒頭沒尾的線索,非但沒能幫他,反而更添了一絲煩亂。
一個一心求死的人,心裡還有挂念?那會是什麼?是他在明朝的妻兒老小?還是別的什麼不為人知的秘密?這絲挂念,是能撬開他嘴巴的縫隙,還是他臨死前的最後一點執念?
無人能給出答案。
盛京城裡的勸降努力,就這樣陷入了僵局。而洪承疇的生命,也如沙漏中的細沙,一點一滴地流向盡頭。
幾天後,宮中設宴,算是為前線的將士們慶功。酒過三巡,菜過五味,皇太極的興致卻始終不高。他端著酒杯,看著殿下歌舞昇平的熱鬧景象,心裡想的還是那個冰冷的囚籠和那個倔強的靈魂。
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帶著幾分酒意,對著滿座的後宮嬪妃和皇子們抱怨道:「松錦一戰,朕俘獲虎將無數,獨獨這個洪承疇,軟硬不吃,真是讓朕寢食難安。滿朝文武,竟無一人能為朕解此憂愁!」
這話一出,殿內的絲竹聲都仿佛弱了下去。嬪妃們個個低眉順眼,大氣不敢出。這種軍國大事,她們哪裡敢插嘴,說對了沒賞,說錯了可能就是一場災禍。
一片寂靜中,只有在筵席的角落裡,一位年僅二十餘歲的年輕妃子——來自科爾沁草原的博爾濟吉特·布木布泰,也就是被封為西宮永福宮側福晉的莊妃,似乎並未受到這壓抑氣氛的影響。
她正低著頭,用她那雙纖細白皙的手,耐心地為身邊年幼的兒子福臨剝著一個金黃的橘子。她的動作很輕柔,很專注,仿佛整個世界的紛擾都與她無關,眼中只有她心愛的兒子和手中的橘子。
可當皇太極那句充滿無奈的抱怨飄進她耳朵里時,她剝橘子的手,幾不可察地微微頓了一下。一片橘絡被她輕輕撕下,她抬起頭,那雙清澈如草原上湖泊的眼眸,越過人群,望向主位上那個愁眉不展的男人。
她的眼神里,沒有旁人的畏懼與惶恐,反而流露出一絲極深的思索,一種仿佛獵人看到獵物時才有的專注與探究。
02
莊妃布木布泰的永福宮,在整個盛京後宮裡,算是一個特別的存在。這裡不像關雎宮宸妃海蘭珠那裡,時常能聽到皇太極爽朗的笑聲;也不像麟趾宮貴妃娜木鐘那裡,總是聚集著一群蒙古來的親貴妃嬪,熱鬧非凡。永福宮總是很安靜,安靜得像它主人的性子一樣,內斂而深沉。
布木布泰並沒有像大多數後宮女子那樣,將自己的一生寄托在爭風吃醋和等待君王的垂青上。對她而言,這深宮大院,既是她的家,也是她的戰場,更是她觀察和學習的課堂。
清晨,當別的妃子還在梳妝打扮時,她已經陪著兒子福臨在窗邊讀書了。她教的,並非死記硬背《三字經》《百家姓》。她會指著書上的「馬」字,給福臨講科爾沁草原上萬馬奔騰的壯闊景象;她會講到「忠」字,給兒子講那些草原上為了部落榮耀而戰死的英雄故事。她總能把那些枯燥的方塊字,變得有血有肉,有聲有色。福臨在她身邊,總是聽得入了迷。
午後,她會親自到宮裡的小花圃里,拿起小鋤頭鬆土。
侍女看不過去,想上來幫忙,她總是笑著擺擺手:「不用,讓我自己來。」她一邊翻動著濕潤的泥土,一邊對侍女蘇茉兒說:「你看,這土和人心是一個道理。你得時常給它鬆動鬆動,透透氣,它才不會板結。土一板結,再好的種子也扎不下去根;人心一板結,再好的道理也聽不進去。」蘇茉兒似懂非懂地點點頭,只覺得娘娘說的話,總是那麼有嚼頭。
布木布泰的智慧,更多時候體現在那些細微的人情世故里。有一次,貴妃娜木鐘宮裡的一個太監,仗著主子得勢,故意找茬,說永福宮的宮女走路沒看道,衝撞了他。那小宮女嚇得臉都白了。布木布泰聽聞後,不急不躁地走了出來,臉上帶著溫和的笑意。
她沒有直接去質問那太監,也沒有為自己的宮女辯護,而是先對那太監說:「喲,這不是李公公嗎?瞧您這身子骨,越發硬朗了。昨兒皇上還夸娜木鐘姐姐宮裡的人懂規矩,想來就是您調教有方。我這宮裡的小丫頭笨手笨腳的,回頭我一定好好說說她。您大人有大量,可千萬別跟她一般見識,氣壞了身子可不值當。」
一番話下來,既捧了娜木鐘,又誇了太監,還順帶把自己的宮女摘了出來。那太監本來是來找茬的,被她這麼一戴高帽,再想發作也拉不下臉來,只好訕訕地說了幾句場面話,灰溜溜地走了。
事後,蘇茉兒佩服得五體投地:「娘娘,您可真厲害!三言兩語就把那個惡人打發了。」
布木布泰只是淡淡一笑,理了理衣袖:「在這宮裡,硬碰硬是最蠢的法子。拳頭打在棉花上,才最讓對方難受。記住,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柔能克剛,也是這個道理。」
她就是這樣,用一種遠超她二十幾歲年齡的沉穩和高情商,在暗流洶湧的後宮中,為自己和兒子福臨撐起了一片安穩的天地。但她的眼光,從未只局限於這四方的宮牆之內。
她不像別的妃子那樣,只關心皇上今晚翻了誰的牌子,賞了誰家珠寶。她更關心皇上的眉毛,是舒展著,還是緊鎖著。
她知道,皇太極的喜怒哀樂,直接關係到大清的國運,也直接關係到她和福臨的未來。她對皇太極的感情是複雜的,不僅僅是夫妻之情,更有一種對草原雄鷹的敬佩,以及將自己命運與之牢牢捆綁在一起的依附感。她清楚地知道,她的榮耀,她兒子的前途,都維繫在皇太極的宏圖偉業之上。
所以,當「洪承疇」這個名字,開始頻繁地出現在從前朝傳到後宮的只言詞組中時,她便敏銳地察覺到,這三個字,已經成了壓在皇太太極心頭的一塊巨石。
每當夜深人靜,皇太極帶著一身疲憊來到永福宮時,布木布泰從不主動去問前朝的煩心事。她只是默默地為他換上舒適的便服,親手端上一碗溫熱的奶茶,或者為他輕輕地按揉著太陽穴。在這樣溫柔而寧靜的氛圍里,皇太極反而會忍不住傾訴幾句。
 呂純弘 • 133K次觀看
呂純弘 • 133K次觀看 呂純弘 • 12K次觀看
呂純弘 • 12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花峰婉 • 17K次觀看
花峰婉 • 17K次觀看 呂純弘 • 10K次觀看
呂純弘 • 10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9K次觀看
呂純弘 • 9K次觀看 奚芝厚 • 9K次觀看
奚芝厚 • 9K次觀看 呂純弘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滿素荷 • 4K次觀看
滿素荷 • 4K次觀看 喬峰傳 • 34K次觀看
喬峰傳 • 34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24K次觀看
呂純弘 • 2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9K次觀看
呂純弘 • 49K次觀看 幸山輪 • 22K次觀看
幸山輪 • 22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