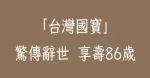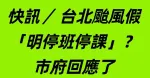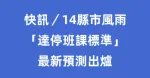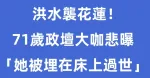4/4
下一頁
崇禎在最後的日子,為何盼不來勤王的救兵?

4/4
袁崇煥像。來源/《中國歷代名人畫像譜》
起初,朱由檢對袁崇煥還是信任的,下旨授予袁崇煥全權調度之權,並催促其「著實剿殺,令達賊匹馬不返」。然而,隨著清軍迅速兵臨北京城下,關寧軍及其他各路勤王兵馬接戰不利,朱由檢的心理防線逐漸崩潰。他聽信了所謂袁崇煥「引敵脅和」的傳聞,在城內不知從何處唱起的「殺了袁崇煥,韃子走一半」的民謠聲中,判處了袁崇煥凌遲的極刑。
然而,處死袁崇煥並不能改善朱由檢對明朝軍隊的觀感,反而令本就有所謂「道德潔癖」的他,在一干習慣於「崇文抑武」的士大夫的影響下,對軍隊日益苛責。
崇禎八年(1635)六月,為了對抗襲擾山西的清軍,遼兵右翼中營參將劉正傑奉調西援,並在清軍撤走後,暫時停駐於當地。這本屬正常的軍事行動,卻由於官場傾軋和土、客軍的矛盾而引發了一場司法訴訟。
對於劉正傑所部的到來,守土有責的宣府巡撫陳新甲自然是歡迎的。但「守備太監」王希忠卻公然上疏稱:「遼將統馭無紀,縱兵淫掠非常!」
為什麼一個太監會如此關心軍紀呢?這個問題還要從朱由檢對太監的特殊使用方式說起:
雖然朱由檢在登基後不久便剷除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但很快卻起用了一批自己的心腹太監,並將其派往各地。
朱由檢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發現自己秉承著「再苦一苦百姓」的原則所加派的「三餉」似乎並沒有切實提升明軍的戰鬥力。懷揣著「銀子都去哪了」的疑問,朱由檢決定派太監去各地核查軍隊數量,以期能夠通過此法來杜絕吃空餉等軍中陋習。
然而,太監無欲並不代表無求,這些人到了地方之後,很快便與地方將佐沆瀣一氣、大肆斂財,明朝軍隊的腐敗非但沒有得到控制,反而由於分贓人員的加入而愈演愈烈。
雖然自己的舉措收效甚微,但朱由檢並不願意就此認輸,他自作聰明地將太監監督軍餉發放的權力改為了由這些人直接籌措和發放軍餉。或許,朱由檢的本意是希望通過太監的自收自支,來實現盈虧平衡。殊不知,這群人比職業官僚更沒道德底線,如深受朱由檢信任的司禮監太監張彝憲便利用鉤校戶部、工部二部出入的機會,大肆斂財,甚至剋扣前線兵器發放。
正是由於視大明的軍餉為自己的錢袋,「守備太監」王希忠才會將劉正傑所部看成「眼中釘、肉中刺」。畢竟,這支客軍的貨幣軍餉自己過不了手,但糧秣物資卻要自己協助籌措。如此一來,站在王希忠的角度,自然急於將這支客軍趕出自己的轄區。
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王希忠派出自己標下旗鼓官姜瓖,串聯了當地的村民,告發劉正傑所部「踏毀田苖、打傷村民」。對於自己心腹太監的上疏,朱由檢高度重視,當即命人著手調查。最終據懷隆兵備道僉事胡福弘調查,劉正傑所部在外出打獵時,的確損毀了一些莊稼,其中一個叫孫大的兵卒更仗著自己是千總蔡仲發的家丁與村民發生口角並引發肢體衝突。
應該說,在明末那個邊軍動輒便「借老鄉頭顱領個軍功」的大環境下,劉正傑所部的軍紀已經可謂嚴明了。因此宣府巡撫陳新甲最終給出的解決方案是把當事人孫大改調邊衛,終身充軍。
陳新甲的意見也得到了時任兵部尚書的張鳳翼與刑部尚書馮英的認可。但朱由檢本人卻並不滿意,要求拿孫大開刀,以達到殺一儆百的效果。一個小小邊軍家丁在朱由檢眼中顯然遠沒有自己的「道德潔癖」來得重要。
朱由檢對軍紀的苛責,最終導致了李自成逼近京師時吳三桂所部關寧軍的緩慢進軍。畢竟,真要在京師城外與李自成決戰,吳三桂會不會成為第二個袁崇煥尚未可知,但關寧軍必定會有不少士卒步孫大的後塵,成為京師毀於兵燹(xiǎn)的「替罪羊」。
值得一提的是,一手促成了「孫大案」的太監王希忠次年死於清軍攻打居庸關的戰鬥之中。而其麾下的旗鼓官姜瓖卻是一路官運亨通,在明末的亂世中成了一方諸侯。
民間武裝=聚眾造反
藩王靠不住、軍隊不可靠,那麼朱由檢乃至整個大明官僚系統對於民間團練武裝的態度又是如何的呢?發生在崇禎十七年(1644)的「許都案」,可謂鮮活的案例。
浙江東陽生員許都的祖父曾任南京兵部尚書,雖然其父名聲不顯。但在當地也算是頭面人物。其年輕時在嘉興求學,曾師從「幾社」重要成員何剛,又為「復社」「幾社」兩社領袖陳子龍賞識,深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思想影響。
然而,儘管許都家世顯赫、交遊廣闊,甚至其友人陳子龍正任紹興府推官,這位無官銜的地方大戶仍未能逃脫知縣姚孫棐的迫害。姚孫棐以加強兵備為名強行攤派收錢,許都因家境尚可,被索要萬兩白銀。無力承擔的許都請求減免,卻遭拒絕。適逢有人假冒司禮監名義在義烏募兵被捕,在典史的唆使下誣指許都同謀。姚孫棐藉機構陷,稱其結黨謀逆,繼續逼索銀兩,甚至威脅按「結社」名單搜捕所謂亂黨。
此時,恰好許都母親去世發喪,送葬者多達萬人。姚孫棐趁機誣告許都謀反。這時,分守道王雄赴任途中因風雪滯留義烏,聞訊即派兵抓捕。許都部下多豪傑之士,義烏、東陽又是強兵之鄉,他的兄弟馮龍友、戴法聰輕鬆打跑了抓捕的差官,送葬民眾在此背景下憤而擁立許都為領袖,以「誅貪吏」為號,頭裹白布,稱「白頭軍」,連克東陽、浦江等多縣,並圍困金華府。
荒誕的是,王雄圍剿失利,許都被困紫薇山。許都擔任監軍的「老朋友」陳子龍受王雄之命,單騎入山勸降,許都信了王雄的「免死」承諾,解散部隊,率二百餘人投降。然而浙江巡按左光先(東林名臣左光斗之弟)與姚孫棐同屬桐城籍,為庇護同鄉,拒不承認承諾。陳子龍先後請求赦免許都、只殺首犯,均被拒絕。最終,許都等六十四人全數被斬。陳子龍因「勸降有功」升任南京吏部主事,卻遭友人徐孚遠、何剛絕交,最終苦悶辭官。
而始作俑者姚孫棐反在左光先庇護下升任兵部主事,後雖入獄,卻因清軍南下獲釋,安然歸老桐城。其家族後人,更出了桐城派文學大家姚鼐。
或許正是因為對民間團練武裝極為敏感,當崇禎十一年(1638)清軍攻打高陽縣城時,早已被革職的名將孫承宗也只能帶著為數不多的家丁和族人登城死戰。其五個兒子、六個孫子、八個侄子孫以及三十餘名婦孺或戰死,或被俘後遇害,只有六子孫鈰之子——六歲的孫之澧及其母躲藏於草叢中而逃生。而據說孫承宗臨死之前,曾豪言道:
「縱然我孫氏一門就算只剩下一個人,也必將剿滅滿清。」
最終竟在機緣巧合之下,孫姓亡清,一語成讖……
起初,朱由檢對袁崇煥還是信任的,下旨授予袁崇煥全權調度之權,並催促其「著實剿殺,令達賊匹馬不返」。然而,隨著清軍迅速兵臨北京城下,關寧軍及其他各路勤王兵馬接戰不利,朱由檢的心理防線逐漸崩潰。他聽信了所謂袁崇煥「引敵脅和」的傳聞,在城內不知從何處唱起的「殺了袁崇煥,韃子走一半」的民謠聲中,判處了袁崇煥凌遲的極刑。
然而,處死袁崇煥並不能改善朱由檢對明朝軍隊的觀感,反而令本就有所謂「道德潔癖」的他,在一干習慣於「崇文抑武」的士大夫的影響下,對軍隊日益苛責。
崇禎八年(1635)六月,為了對抗襲擾山西的清軍,遼兵右翼中營參將劉正傑奉調西援,並在清軍撤走後,暫時停駐於當地。這本屬正常的軍事行動,卻由於官場傾軋和土、客軍的矛盾而引發了一場司法訴訟。
對於劉正傑所部的到來,守土有責的宣府巡撫陳新甲自然是歡迎的。但「守備太監」王希忠卻公然上疏稱:「遼將統馭無紀,縱兵淫掠非常!」
為什麼一個太監會如此關心軍紀呢?這個問題還要從朱由檢對太監的特殊使用方式說起:
雖然朱由檢在登基後不久便剷除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但很快卻起用了一批自己的心腹太監,並將其派往各地。
朱由檢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發現自己秉承著「再苦一苦百姓」的原則所加派的「三餉」似乎並沒有切實提升明軍的戰鬥力。懷揣著「銀子都去哪了」的疑問,朱由檢決定派太監去各地核查軍隊數量,以期能夠通過此法來杜絕吃空餉等軍中陋習。
然而,太監無欲並不代表無求,這些人到了地方之後,很快便與地方將佐沆瀣一氣、大肆斂財,明朝軍隊的腐敗非但沒有得到控制,反而由於分贓人員的加入而愈演愈烈。
雖然自己的舉措收效甚微,但朱由檢並不願意就此認輸,他自作聰明地將太監監督軍餉發放的權力改為了由這些人直接籌措和發放軍餉。或許,朱由檢的本意是希望通過太監的自收自支,來實現盈虧平衡。殊不知,這群人比職業官僚更沒道德底線,如深受朱由檢信任的司禮監太監張彝憲便利用鉤校戶部、工部二部出入的機會,大肆斂財,甚至剋扣前線兵器發放。
正是由於視大明的軍餉為自己的錢袋,「守備太監」王希忠才會將劉正傑所部看成「眼中釘、肉中刺」。畢竟,這支客軍的貨幣軍餉自己過不了手,但糧秣物資卻要自己協助籌措。如此一來,站在王希忠的角度,自然急於將這支客軍趕出自己的轄區。
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王希忠派出自己標下旗鼓官姜瓖,串聯了當地的村民,告發劉正傑所部「踏毀田苖、打傷村民」。對於自己心腹太監的上疏,朱由檢高度重視,當即命人著手調查。最終據懷隆兵備道僉事胡福弘調查,劉正傑所部在外出打獵時,的確損毀了一些莊稼,其中一個叫孫大的兵卒更仗著自己是千總蔡仲發的家丁與村民發生口角並引發肢體衝突。
應該說,在明末那個邊軍動輒便「借老鄉頭顱領個軍功」的大環境下,劉正傑所部的軍紀已經可謂嚴明了。因此宣府巡撫陳新甲最終給出的解決方案是把當事人孫大改調邊衛,終身充軍。
陳新甲的意見也得到了時任兵部尚書的張鳳翼與刑部尚書馮英的認可。但朱由檢本人卻並不滿意,要求拿孫大開刀,以達到殺一儆百的效果。一個小小邊軍家丁在朱由檢眼中顯然遠沒有自己的「道德潔癖」來得重要。
朱由檢對軍紀的苛責,最終導致了李自成逼近京師時吳三桂所部關寧軍的緩慢進軍。畢竟,真要在京師城外與李自成決戰,吳三桂會不會成為第二個袁崇煥尚未可知,但關寧軍必定會有不少士卒步孫大的後塵,成為京師毀於兵燹(xiǎn)的「替罪羊」。
值得一提的是,一手促成了「孫大案」的太監王希忠次年死於清軍攻打居庸關的戰鬥之中。而其麾下的旗鼓官姜瓖卻是一路官運亨通,在明末的亂世中成了一方諸侯。
民間武裝=聚眾造反
藩王靠不住、軍隊不可靠,那麼朱由檢乃至整個大明官僚系統對於民間團練武裝的態度又是如何的呢?發生在崇禎十七年(1644)的「許都案」,可謂鮮活的案例。
浙江東陽生員許都的祖父曾任南京兵部尚書,雖然其父名聲不顯。但在當地也算是頭面人物。其年輕時在嘉興求學,曾師從「幾社」重要成員何剛,又為「復社」「幾社」兩社領袖陳子龍賞識,深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思想影響。
然而,儘管許都家世顯赫、交遊廣闊,甚至其友人陳子龍正任紹興府推官,這位無官銜的地方大戶仍未能逃脫知縣姚孫棐的迫害。姚孫棐以加強兵備為名強行攤派收錢,許都因家境尚可,被索要萬兩白銀。無力承擔的許都請求減免,卻遭拒絕。適逢有人假冒司禮監名義在義烏募兵被捕,在典史的唆使下誣指許都同謀。姚孫棐藉機構陷,稱其結黨謀逆,繼續逼索銀兩,甚至威脅按「結社」名單搜捕所謂亂黨。
此時,恰好許都母親去世發喪,送葬者多達萬人。姚孫棐趁機誣告許都謀反。這時,分守道王雄赴任途中因風雪滯留義烏,聞訊即派兵抓捕。許都部下多豪傑之士,義烏、東陽又是強兵之鄉,他的兄弟馮龍友、戴法聰輕鬆打跑了抓捕的差官,送葬民眾在此背景下憤而擁立許都為領袖,以「誅貪吏」為號,頭裹白布,稱「白頭軍」,連克東陽、浦江等多縣,並圍困金華府。
荒誕的是,王雄圍剿失利,許都被困紫薇山。許都擔任監軍的「老朋友」陳子龍受王雄之命,單騎入山勸降,許都信了王雄的「免死」承諾,解散部隊,率二百餘人投降。然而浙江巡按左光先(東林名臣左光斗之弟)與姚孫棐同屬桐城籍,為庇護同鄉,拒不承認承諾。陳子龍先後請求赦免許都、只殺首犯,均被拒絕。最終,許都等六十四人全數被斬。陳子龍因「勸降有功」升任南京吏部主事,卻遭友人徐孚遠、何剛絕交,最終苦悶辭官。
而始作俑者姚孫棐反在左光先庇護下升任兵部主事,後雖入獄,卻因清軍南下獲釋,安然歸老桐城。其家族後人,更出了桐城派文學大家姚鼐。
或許正是因為對民間團練武裝極為敏感,當崇禎十一年(1638)清軍攻打高陽縣城時,早已被革職的名將孫承宗也只能帶著為數不多的家丁和族人登城死戰。其五個兒子、六個孫子、八個侄子孫以及三十餘名婦孺或戰死,或被俘後遇害,只有六子孫鈰之子——六歲的孫之澧及其母躲藏於草叢中而逃生。而據說孫承宗臨死之前,曾豪言道:
「縱然我孫氏一門就算只剩下一個人,也必將剿滅滿清。」
最終竟在機緣巧合之下,孫姓亡清,一語成讖……
 呂純弘 • 139K次觀看
呂純弘 • 139K次觀看 呂純弘 • 12K次觀看
呂純弘 • 12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花峰婉 • 17K次觀看
花峰婉 • 17K次觀看 呂純弘 • 10K次觀看
呂純弘 • 10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9K次觀看
呂純弘 • 9K次觀看 奚芝厚 • 9K次觀看
奚芝厚 • 9K次觀看 呂純弘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7K次觀看 滿素荷 • 4K次觀看
滿素荷 • 4K次觀看 喬峰傳 • 34K次觀看
喬峰傳 • 34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24K次觀看
呂純弘 • 2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9K次觀看
呂純弘 • 49K次觀看 幸山輪 • 22K次觀看
幸山輪 • 22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