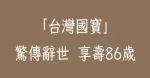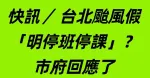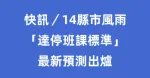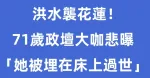1/3
下一頁
朱安:婚後無愛無性,照顧婆婆37年,想與魯迅合葬卻遭許廣平拒絕

1/3
朱安:婚後無愛無性,照顧婆婆37年,想與魯迅合葬卻遭許廣平拒絕
在北京西三條二十一號一所小四合院裡,居住著一位婦人:她身材瘦小,臉又瘦又長,而且顴骨突出,由於纏足,走路顫顫巍巍的。
她跟名義上的丈夫各處一室,每天基本上只有三次對話:
一、叫早。回答是:「哼。」
二、臨睡,問關不關北房過道的中門。回答是:「關」,或「不關」。
三、索要家用錢。回答是:「多少」?然後照付。
為了儘可能少費口舌,名義上的丈夫將換洗的衣物放在柳條箱的蓋上,塞在自己的床底下,她支配傭人洗凈之後,疊放在柳條箱內,上面蓋一層白布,放在她臥室的門旁。
這位婦人就是魯迅的原配夫人朱安。
1878年,朱安出生在浙江紹興城裡的丁家弄。
她和魯迅的婚姻是兩家大人包辦的產物,而且魯迅的母親非常喜歡朱安,於是就挽了媒人去說合。
但魯迅在日本知道後,很反對,來信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
但是魯瑞則叫魯迅的堂叔周冠五寫信勸說魯迅,強調這婚事原是她求親求來的,不能退聘,否則,悔婚於周家朱家名譽都不好,朱家姑娘更沒人要娶了。
作為讓步,魯迅又提出希望女方放足、進學堂,但是因為種種原因,朱安並沒有這樣做。
不過後來魯迅雖然覺得有些勉強,但認為既是母親作了主,就沒有堅決反對,也許他信任母親,認為母親給他找的人,總不會錯的。
1899年,21歲的朱安和魯迅訂婚,但是直到28歲那年她才嫁到周家。
1906年農曆六月初六,朱安與魯迅在周家新台門的大廳舉行了婚禮。
從1899年與周家少爺訂婚到二人舉行結婚儀式,朱安等了七年,終於等來了這一天。
不過她也聽說周家少爺對這樁婚事不太滿意。
也許,就是在長達七年的近乎絕望的等待中,她記住了長輩們常在她耳邊說的那句話:「生為周家人,死為周家鬼。」
按當時紹興風俗,如果姑娘被男家退聘,無異於被宣判了死刑,是家族的恥辱。所以在朱安的心裡,就是,既然和周家少爺訂了婚,那麼她死也要死在周家,她沒有退路。
多年以後魯老太太懷著內疚對人說起她把魯迅騙回國的事情:
「…倒是朱家以女兒年紀大了,一再托媒人來催,希望儘快辦理婚事。因為他們聽到外面有些不三不四的謠言,說大先生已娶了日本老婆,生了孩子……我實在被纏不過,只得託人打電報給大先生,騙他說我病了,叫他速歸。大先生果然回來了,我向他說明原因,他倒也不見怪,同意結婚。」
由於魯迅不喜歡小腳,結婚當天,朱安給自己弄了一雙假大腳,就是穿上大一號的鞋子,假裝大腳。
魯迅對朱安沒有好感,尤其是見過新式女性以後,
他看著自己的新夫人還裹著三寸金蓮,就覺得兩人更加格格不入,尤其是她結婚當天又用假大腳糊弄,而且因為她又瘦又小,又穿上一雙大鞋,導致她下轎時,「上不著天,下不著地」,鞋子就掉下來了,或許這讓魯迅對她更加反感了。
朱安這樣被魯迅厭惡,那他們的新婚之夜,朱安註定是要獨守空房的。
那天晚上,魯迅睡在母親房中,朱安一人獨守空房。
當時照老例新婚夫婦是要去老台門拜祠堂的,因為魯迅對這樁婚姻不滿意,就沒有去。
第二夜,魯迅睡到了書房。
據他的傭工王鶴照透露,「魯迅新婚後的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臉,讓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頭埋在被子裡哭了」。
可見,魯迅有多麼失望。
對此,周建人的解釋是因為朱安既不識字,也沒有放足:「結婚以後,我大哥發現新娘子既不識字,也沒有放足,他以前寫來的信,統統都是白寫。」
周作人則說「新人極為矮小,頗有發育不全的樣子」。
世人都覺得這樁婚姻受苦的是魯迅,但是誰能考慮一下朱安的感受呢,她作為一個裹小腳的女人,命運不由得自己做主,對所所有新婚的女子來說,
新婚夜是她們最幸福的時刻,可是對於朱安來說,新婚夜則是她後半身悲劇的開始,在新婚之後的三四天裡,她坐在屋裡一邊流淚一邊聽過來人教她如何慢慢熬,總會熬到魯迅回心轉意的那一天。
婚後幾天,魯迅就出去上學了,朱安作為「新婦」則留在家中照顧婆婆,雖然這樣的生活朱安來說很殘忍,但是朱安已經心滿意足了,不管怎樣,魯迅沒有食言,把她娶進了周家的大門,成了周家的人。
七年後,也就是1909年,在母親的催促下,魯迅終於回來了。
朱安本以為這次丈夫回來,他對自己的態度會有所改變,因為小別勝新婚,再說他們一別七年。
但是,魯迅的態度很快讓她心涼了。
這一年多的時間,魯迅在紹興教書,雖然同住在一個屋檐下,但是魯迅很少回家,就是回家也非常晚,而且也是獨自睡,也不和朱安說話。
用魯瑞的話說「他們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時不多說話,但沒有感情,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
天天低頭不見抬頭見,魯迅也曾試圖跟朱安講話,可是朱安一開口,就讓他感到話不投機半句多,從此再也不願意跟她說話。
有一次,魯迅告訴朱安,日本有一種東西很好吃,朱安趕緊說是的,是的,她也吃過的。
魯迅說其實這種東西不但紹興沒有,就是全中國也沒有,她怎麼能吃到?這樣,談不下去了。談話不是對手,沒趣味,不如不談…
在魯迅看看,朱安是自作聰明,或許朱安只是想就著這個話題和魯迅多聊幾句。
1912年初,魯迅又離開家了,這一走又是7年。
從此,朱安又開始了長達七年的獨居生活。
期間,朱安曾經讓弟弟給魯迅寫過信,但是魯迅對她的信置之不理,根本沒有回覆。
一次,魯迅回紹興探親,朱安做了一大桌子菜招待親朋好友,朱安在飯桌上指責了對魯迅的種種不是,但是魯迅一句話也不說,任她發揮。
事後魯迅對孫伏園說:「她是有意挑釁,我如答辯,就會中了她的計而鬧得一塌糊塗;置之不理,她也就無計可施了。」
周作人曾經在日記里記錄,從1914年開始,朱安開始頻頻回娘家,有時候會待上十幾天,甚至更長時間,有一次,她竟然在娘家住了兩個月。
朱安的這一舉動,不能不讓人感到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逃避。
1919年,魯迅老家的老房子要被賣掉,他則在北京買下了八道灣的宅子,把一大家人都接到了北京,也包括朱安。
「在紹興這地方,要讓一個女人離開夫家,幾乎是不可能的。按照不成文的規矩,如果婦女離開了夫家,或者丈夫死了改嫁,那麼即便有兒子,也「不得母之」,不允許載入家譜中,死後也就得不到歸宿。她們不僅不容於家族,也不容於社會,被人們看不起,很難找到活路,結局往往比守節還要悲慘。」
雖然他討厭朱安,但是朱安長年累月侍奉母親魯瑞,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何況她一個女人家,也無地方可去。
對朱安來說,去北京並沒有感到很開心,因為老房子沒有了,即便之後她在北京待不下去了,也無處可去。
這時候的朱安40歲,這次她離開故土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去過。
在八道灣住了幾年後,因魯迅和周作人失和搬了出去。
朱安作為八道灣內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沒人在意她對這件事什麼態度,當魯迅決定搬出八道灣時,她也做出了一個決定:離開八道灣,和魯迅一起搬出去住。
關於是否搬出去住,魯迅是徵求過朱安的意見的,問她是留在八道灣還是還是回紹興朱家?又說如果回紹興他將按月寄錢供應朱安的生活。
朱安回復他,
「八道灣我不能住,因為你搬出去,娘娘(太師母)遲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獨個人跟著叔嬸侄兒侄女過,算什麼呢?再說嬸嬸是日本人,話都聽不懂,日子不好過呵。紹興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磚塔胡同,橫豎總要人替你燒飯、縫補、洗衣、掃地的,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1924年5月25,朱安跟著,魯迅,婆婆路魯瑞遷居到西三條胡同21號的住宅,開始了他們在新家的生活。
遷入磚塔胡同不久,就病倒了,朱安對魯迅照顧得事無巨細。
魯迅當時不能吃飯,只能吃粥,朱安每次燒粥前,先把米弄碎,燒成容易消化的粥糊,並託人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買糟雞、熟火腿、肉鬆等魯迅平時喜歡吃的菜,給他下粥,讓他開胃,可是朱安卻不吃這些好菜。
朱安每天會從飯菜的剩餘來判斷魯迅對這道菜是否喜歡,如果喜歡的話下一次做菜時,就多做一些。
雖然兩人都在同一屋檐下,雖然魯迅默認朱安對他的照顧,但是兩人依然是各過各的,像個陌生人一樣,魯迅很少和朱安說話。
1925年夏天,朱安生病了,住在日本人山本開的醫院裡。
魯迅一進門,就問朱安:「檢驗過了沒有?」
朱安說:「檢驗過了。」魯迅就往外走,嘴裡還說著:「我問問醫生去。」
過一刻,魯迅回來了,直接和朋友說「走罷,到我家裡吃中飯去。」
這時朱安問他「醫生怎麼說?」
魯迅只簡單地回答:「沒有什麼,多養幾天就好了。」說完,就匆匆走出了病房。
對魯迅來說,他只是對朱安盡了義務,卻不願在病房多逗留一刻陪伴她,也不願多說一句安慰溫存的話。
雖然魯迅對朱安很冷漠,但是母親魯瑞還是非常認可自己親自挑選的兒媳婦的,多年的相處,她把朱安看做自己身邊貼心的人,很希望兒子兒媳有一天能好起來。
一次,魯瑞看到兒子大冬天的還穿著單薄的衣褲,就責怪朱安,「無怪乎他不喜歡你,到冬天了,也不給他縫條新棉褲。」
於是朱安奉老太太的命令做了一條新棉褲,等魯迅不在家的時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換上,沒想到魯迅竟把新棉褲扔了出來。
朱安得知後,更加心灰意冷了。
不過朱安並不只是一味的隱忍,她也有反抗的時候。
一次,親朋好友給魯瑞過大壽,開席之前,朱安忽然穿戴整齊走出來,向親友下了一跪,說道:「我來周家已許多年,大先生(指魯迅)不很理我,但我也不會離開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後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
說完話,叩了頭,退回房去。
當時赴宴的應該是魯迅身邊的同事和老友,朱安用這樣一個激烈的舉動,爭取到了大家的同情,也算是將了魯迅一軍。
1926年8月,魯迅和許廣平離開了北京,朱安和婆婆站在西三條的門口,目送他遠去的身影,直到消失在胡同盡頭。
不久後,朱安便聽說周海嬰出生的消息,她非常高興,這時候的朱安也50齣頭了,她自己不可能有孩子了。
「按紹興習俗,沒有孩子,也屬婦人的一個「過錯」。現在有了海嬰,他是大先生的兒子,自然也是她的兒子。而且她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她想到有了海嬰,死後有海嬰給她燒紙,送羹飯,送寒衣……閻羅大王不會認為她是孤魂野鬼,罰她下地獄,讓她挨餓受凍的。於是她精神上得到了安慰,所以很高興」。
自從魯迅離開北京後,朱安的生活似乎更和他無關了,兩人十年間的聯繫是以「家用帳」維持著彼此的關係,這也間接證明朱安沒有看錯人,至少,魯迅會維持她的生活。
魯迅和許廣平在上海有了他們的三口之家,再北京的西三條胡同,朱安與婆婆相伴,默默地度著她的餘生。她知道自己這輩子就這樣過了,這一輩子也只有婆婆對她不離不棄。
1936年,魯迅在上海去世。魯迅的去世,對朱安和婆婆都是個沉重的打擊。
朱安本想帶著婆婆一起去上海,但此時的朱安也將近花甲,婆婆也年事已高,走路都需要人攙扶,她們去上海是不可能的。
朱安就在北京的家裡為魯迅設了靈堂,祭奠了魯迅,放了魯迅生前喜歡吃的菜肴,用白薯蕷切片,雞蛋和麵粉塗之加油炸熟。
之後,每年魯迅忌日,當社會各界舉行各種紀念儀式時,朱安也會在西三條的家裡,在靈台前供上魯迅生前愛吃的食物,為他焚香默禱。
她用她自己的方式表達著心底的那一份情意。
魯迅去世後,朱安托周建人的許廣平寫信,希望她能帶著孩子到北京居住。
不過,許廣平作為一個現代女性,她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這樣的安排的。更不願意把自己納入這樣一個舊家庭的格局。
魯迅走了,朱安和婆婆的經濟來源,主要是許廣平寄來的魯迅著作的版稅,以及之前攢下的積蓄。
1943年,87歲的魯瑞去世。
朱安為婆婆送了終,自此,西三條只剩下她一個孤單的身影。
在北京西三條二十一號一所小四合院裡,居住著一位婦人:她身材瘦小,臉又瘦又長,而且顴骨突出,由於纏足,走路顫顫巍巍的。
她跟名義上的丈夫各處一室,每天基本上只有三次對話:
一、叫早。回答是:「哼。」
二、臨睡,問關不關北房過道的中門。回答是:「關」,或「不關」。
三、索要家用錢。回答是:「多少」?然後照付。
為了儘可能少費口舌,名義上的丈夫將換洗的衣物放在柳條箱的蓋上,塞在自己的床底下,她支配傭人洗凈之後,疊放在柳條箱內,上面蓋一層白布,放在她臥室的門旁。
這位婦人就是魯迅的原配夫人朱安。
1878年,朱安出生在浙江紹興城裡的丁家弄。
她和魯迅的婚姻是兩家大人包辦的產物,而且魯迅的母親非常喜歡朱安,於是就挽了媒人去說合。
但魯迅在日本知道後,很反對,來信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
但是魯瑞則叫魯迅的堂叔周冠五寫信勸說魯迅,強調這婚事原是她求親求來的,不能退聘,否則,悔婚於周家朱家名譽都不好,朱家姑娘更沒人要娶了。
作為讓步,魯迅又提出希望女方放足、進學堂,但是因為種種原因,朱安並沒有這樣做。
不過後來魯迅雖然覺得有些勉強,但認為既是母親作了主,就沒有堅決反對,也許他信任母親,認為母親給他找的人,總不會錯的。
1899年,21歲的朱安和魯迅訂婚,但是直到28歲那年她才嫁到周家。
1906年農曆六月初六,朱安與魯迅在周家新台門的大廳舉行了婚禮。
從1899年與周家少爺訂婚到二人舉行結婚儀式,朱安等了七年,終於等來了這一天。
不過她也聽說周家少爺對這樁婚事不太滿意。
也許,就是在長達七年的近乎絕望的等待中,她記住了長輩們常在她耳邊說的那句話:「生為周家人,死為周家鬼。」
按當時紹興風俗,如果姑娘被男家退聘,無異於被宣判了死刑,是家族的恥辱。所以在朱安的心裡,就是,既然和周家少爺訂了婚,那麼她死也要死在周家,她沒有退路。
多年以後魯老太太懷著內疚對人說起她把魯迅騙回國的事情:
「…倒是朱家以女兒年紀大了,一再托媒人來催,希望儘快辦理婚事。因為他們聽到外面有些不三不四的謠言,說大先生已娶了日本老婆,生了孩子……我實在被纏不過,只得託人打電報給大先生,騙他說我病了,叫他速歸。大先生果然回來了,我向他說明原因,他倒也不見怪,同意結婚。」
由於魯迅不喜歡小腳,結婚當天,朱安給自己弄了一雙假大腳,就是穿上大一號的鞋子,假裝大腳。
魯迅對朱安沒有好感,尤其是見過新式女性以後,
他看著自己的新夫人還裹著三寸金蓮,就覺得兩人更加格格不入,尤其是她結婚當天又用假大腳糊弄,而且因為她又瘦又小,又穿上一雙大鞋,導致她下轎時,「上不著天,下不著地」,鞋子就掉下來了,或許這讓魯迅對她更加反感了。
朱安這樣被魯迅厭惡,那他們的新婚之夜,朱安註定是要獨守空房的。
那天晚上,魯迅睡在母親房中,朱安一人獨守空房。
當時照老例新婚夫婦是要去老台門拜祠堂的,因為魯迅對這樁婚姻不滿意,就沒有去。
第二夜,魯迅睡到了書房。
據他的傭工王鶴照透露,「魯迅新婚後的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臉,讓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頭埋在被子裡哭了」。
可見,魯迅有多麼失望。
對此,周建人的解釋是因為朱安既不識字,也沒有放足:「結婚以後,我大哥發現新娘子既不識字,也沒有放足,他以前寫來的信,統統都是白寫。」
周作人則說「新人極為矮小,頗有發育不全的樣子」。
世人都覺得這樁婚姻受苦的是魯迅,但是誰能考慮一下朱安的感受呢,她作為一個裹小腳的女人,命運不由得自己做主,對所所有新婚的女子來說,
新婚夜是她們最幸福的時刻,可是對於朱安來說,新婚夜則是她後半身悲劇的開始,在新婚之後的三四天裡,她坐在屋裡一邊流淚一邊聽過來人教她如何慢慢熬,總會熬到魯迅回心轉意的那一天。
婚後幾天,魯迅就出去上學了,朱安作為「新婦」則留在家中照顧婆婆,雖然這樣的生活朱安來說很殘忍,但是朱安已經心滿意足了,不管怎樣,魯迅沒有食言,把她娶進了周家的大門,成了周家的人。
七年後,也就是1909年,在母親的催促下,魯迅終於回來了。
朱安本以為這次丈夫回來,他對自己的態度會有所改變,因為小別勝新婚,再說他們一別七年。
但是,魯迅的態度很快讓她心涼了。
這一年多的時間,魯迅在紹興教書,雖然同住在一個屋檐下,但是魯迅很少回家,就是回家也非常晚,而且也是獨自睡,也不和朱安說話。
用魯瑞的話說「他們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時不多說話,但沒有感情,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
天天低頭不見抬頭見,魯迅也曾試圖跟朱安講話,可是朱安一開口,就讓他感到話不投機半句多,從此再也不願意跟她說話。
有一次,魯迅告訴朱安,日本有一種東西很好吃,朱安趕緊說是的,是的,她也吃過的。
魯迅說其實這種東西不但紹興沒有,就是全中國也沒有,她怎麼能吃到?這樣,談不下去了。談話不是對手,沒趣味,不如不談…
在魯迅看看,朱安是自作聰明,或許朱安只是想就著這個話題和魯迅多聊幾句。
1912年初,魯迅又離開家了,這一走又是7年。
從此,朱安又開始了長達七年的獨居生活。
期間,朱安曾經讓弟弟給魯迅寫過信,但是魯迅對她的信置之不理,根本沒有回覆。
一次,魯迅回紹興探親,朱安做了一大桌子菜招待親朋好友,朱安在飯桌上指責了對魯迅的種種不是,但是魯迅一句話也不說,任她發揮。
事後魯迅對孫伏園說:「她是有意挑釁,我如答辯,就會中了她的計而鬧得一塌糊塗;置之不理,她也就無計可施了。」
周作人曾經在日記里記錄,從1914年開始,朱安開始頻頻回娘家,有時候會待上十幾天,甚至更長時間,有一次,她竟然在娘家住了兩個月。
朱安的這一舉動,不能不讓人感到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逃避。
1919年,魯迅老家的老房子要被賣掉,他則在北京買下了八道灣的宅子,把一大家人都接到了北京,也包括朱安。
「在紹興這地方,要讓一個女人離開夫家,幾乎是不可能的。按照不成文的規矩,如果婦女離開了夫家,或者丈夫死了改嫁,那麼即便有兒子,也「不得母之」,不允許載入家譜中,死後也就得不到歸宿。她們不僅不容於家族,也不容於社會,被人們看不起,很難找到活路,結局往往比守節還要悲慘。」
雖然他討厭朱安,但是朱安長年累月侍奉母親魯瑞,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何況她一個女人家,也無地方可去。
對朱安來說,去北京並沒有感到很開心,因為老房子沒有了,即便之後她在北京待不下去了,也無處可去。
這時候的朱安40歲,這次她離開故土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去過。
在八道灣住了幾年後,因魯迅和周作人失和搬了出去。
朱安作為八道灣內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沒人在意她對這件事什麼態度,當魯迅決定搬出八道灣時,她也做出了一個決定:離開八道灣,和魯迅一起搬出去住。
關於是否搬出去住,魯迅是徵求過朱安的意見的,問她是留在八道灣還是還是回紹興朱家?又說如果回紹興他將按月寄錢供應朱安的生活。
朱安回復他,
「八道灣我不能住,因為你搬出去,娘娘(太師母)遲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獨個人跟著叔嬸侄兒侄女過,算什麼呢?再說嬸嬸是日本人,話都聽不懂,日子不好過呵。紹興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磚塔胡同,橫豎總要人替你燒飯、縫補、洗衣、掃地的,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1924年5月25,朱安跟著,魯迅,婆婆路魯瑞遷居到西三條胡同21號的住宅,開始了他們在新家的生活。
遷入磚塔胡同不久,就病倒了,朱安對魯迅照顧得事無巨細。
魯迅當時不能吃飯,只能吃粥,朱安每次燒粥前,先把米弄碎,燒成容易消化的粥糊,並託人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買糟雞、熟火腿、肉鬆等魯迅平時喜歡吃的菜,給他下粥,讓他開胃,可是朱安卻不吃這些好菜。
朱安每天會從飯菜的剩餘來判斷魯迅對這道菜是否喜歡,如果喜歡的話下一次做菜時,就多做一些。
雖然兩人都在同一屋檐下,雖然魯迅默認朱安對他的照顧,但是兩人依然是各過各的,像個陌生人一樣,魯迅很少和朱安說話。
1925年夏天,朱安生病了,住在日本人山本開的醫院裡。
魯迅一進門,就問朱安:「檢驗過了沒有?」
朱安說:「檢驗過了。」魯迅就往外走,嘴裡還說著:「我問問醫生去。」
過一刻,魯迅回來了,直接和朋友說「走罷,到我家裡吃中飯去。」
這時朱安問他「醫生怎麼說?」
魯迅只簡單地回答:「沒有什麼,多養幾天就好了。」說完,就匆匆走出了病房。
對魯迅來說,他只是對朱安盡了義務,卻不願在病房多逗留一刻陪伴她,也不願多說一句安慰溫存的話。
雖然魯迅對朱安很冷漠,但是母親魯瑞還是非常認可自己親自挑選的兒媳婦的,多年的相處,她把朱安看做自己身邊貼心的人,很希望兒子兒媳有一天能好起來。
一次,魯瑞看到兒子大冬天的還穿著單薄的衣褲,就責怪朱安,「無怪乎他不喜歡你,到冬天了,也不給他縫條新棉褲。」
於是朱安奉老太太的命令做了一條新棉褲,等魯迅不在家的時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換上,沒想到魯迅竟把新棉褲扔了出來。
朱安得知後,更加心灰意冷了。
不過朱安並不只是一味的隱忍,她也有反抗的時候。
一次,親朋好友給魯瑞過大壽,開席之前,朱安忽然穿戴整齊走出來,向親友下了一跪,說道:「我來周家已許多年,大先生(指魯迅)不很理我,但我也不會離開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後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
說完話,叩了頭,退回房去。
當時赴宴的應該是魯迅身邊的同事和老友,朱安用這樣一個激烈的舉動,爭取到了大家的同情,也算是將了魯迅一軍。
1926年8月,魯迅和許廣平離開了北京,朱安和婆婆站在西三條的門口,目送他遠去的身影,直到消失在胡同盡頭。
不久後,朱安便聽說周海嬰出生的消息,她非常高興,這時候的朱安也50齣頭了,她自己不可能有孩子了。
「按紹興習俗,沒有孩子,也屬婦人的一個「過錯」。現在有了海嬰,他是大先生的兒子,自然也是她的兒子。而且她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她想到有了海嬰,死後有海嬰給她燒紙,送羹飯,送寒衣……閻羅大王不會認為她是孤魂野鬼,罰她下地獄,讓她挨餓受凍的。於是她精神上得到了安慰,所以很高興」。
自從魯迅離開北京後,朱安的生活似乎更和他無關了,兩人十年間的聯繫是以「家用帳」維持著彼此的關係,這也間接證明朱安沒有看錯人,至少,魯迅會維持她的生活。
魯迅和許廣平在上海有了他們的三口之家,再北京的西三條胡同,朱安與婆婆相伴,默默地度著她的餘生。她知道自己這輩子就這樣過了,這一輩子也只有婆婆對她不離不棄。
1936年,魯迅在上海去世。魯迅的去世,對朱安和婆婆都是個沉重的打擊。
朱安本想帶著婆婆一起去上海,但此時的朱安也將近花甲,婆婆也年事已高,走路都需要人攙扶,她們去上海是不可能的。
朱安就在北京的家裡為魯迅設了靈堂,祭奠了魯迅,放了魯迅生前喜歡吃的菜肴,用白薯蕷切片,雞蛋和麵粉塗之加油炸熟。
之後,每年魯迅忌日,當社會各界舉行各種紀念儀式時,朱安也會在西三條的家裡,在靈台前供上魯迅生前愛吃的食物,為他焚香默禱。
她用她自己的方式表達著心底的那一份情意。
魯迅去世後,朱安托周建人的許廣平寫信,希望她能帶著孩子到北京居住。
不過,許廣平作為一個現代女性,她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這樣的安排的。更不願意把自己納入這樣一個舊家庭的格局。
魯迅走了,朱安和婆婆的經濟來源,主要是許廣平寄來的魯迅著作的版稅,以及之前攢下的積蓄。
1943年,87歲的魯瑞去世。
朱安為婆婆送了終,自此,西三條只剩下她一個孤單的身影。
 呂純弘 • 133K次觀看
呂純弘 • 133K次觀看 呂純弘 • 12K次觀看
呂純弘 • 12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花峰婉 • 17K次觀看
花峰婉 • 17K次觀看 呂純弘 • 10K次觀看
呂純弘 • 10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9K次觀看
呂純弘 • 9K次觀看 奚芝厚 • 9K次觀看
奚芝厚 • 9K次觀看 呂純弘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23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滿素荷 • 4K次觀看
滿素荷 • 4K次觀看 喬峰傳 • 34K次觀看
喬峰傳 • 34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24K次觀看
呂純弘 • 2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9K次觀看
呂純弘 • 49K次觀看 幸山輪 • 22K次觀看
幸山輪 • 22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